2021-04-08 | PChome書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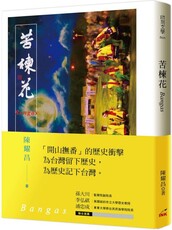
 苦楝花Bangas
苦楝花Bangas
作者:陳耀昌 出版社:印刻 出版日期:2019-06-28 00:00:00
<內容簡介>
「開山撫番」的歷史衝擊!
為台灣留下歷史,為歷史記下台灣
三個後山原住民族「被開山撫番」的故事。
陳耀昌賦予原住民的角度與感受。
〈奇密花〉
她不自覺地流下眼淚來。這個操場就是整整一百四十一年前,吳光亮屠殺原住民的地方,現在稱為「大港口事件」的發生地。而其實,大港口事件只是眾多戰役及大屠殺的一節。她回到操場邊,昨夜的槍聲及慘叫聲又在他腦中響起。她跪了下來,向埋在地下的亡靈表示歉意。
〈苦楝花〉(撒奇萊雅語Bangas)
撒奇萊雅的故事,從來沒有戰爭。撒奇萊雅的故事,頂多只有喜歡嚇人的巨人阿里嘎該。撒奇萊雅的故事,頂多是會欺騙小孩的的阿里嘎該。撒奇萊雅的地域從未有戰爭,撒奇萊雅不要戰爭。木神Sakul啊,撒奇萊雅不要戰爭,但是白浪敵人一直侵凌加禮宛及撒族。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所以撒族過去從未有戰爭。人既犯我撒族,撒族抵抗有錯嗎?
〈大庄阿桃〉
萬一像加禮宛的事也發生在我們大庄,Taiovan族的歷史必須永遠流傳下去。所以我希望大家保持警覺。每一家都必須準備一些食物,如果官兵真的來了,我們必須到山中去躲一陣子。
★本書特色:
繼《傀儡花》《獅頭花》之後,「台灣三部曲」最後一部《苦楝花》重磅上市!
★名人推薦:
孫大川│監察院副院長
李弘祺│美國紐約市立大學歷史教授
浦忠成│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院長
──聯合推薦
陳醫師在本書寫後感言裡,清楚交代了自己在田野調查中見到的人和種種令人驚嘆的巧遇。文學創作的本領,讓他有更大的空間、更大的想像力和自由,去填補文字和文獻無法記錄的聲音,從族人飄渺的口傳記憶裡,讓歷史重新說話。──孫大川
陳醫師有一個重要的使命,那就是讓這些小説同時得到解釋,好「發明」或「再現」十九世紀的「開山撫番」歷史。顯然地,這個使命是沉重的,而它的展現則是燦爛的。──李弘祺
陳耀昌醫師的努力尋訪,讓這些故事/歷史再次被擦亮。這本《苦楝花》應該可以讓行遊東部縱谷與東海岸的旅人得以增添更多歷史/故事探索的興味。──浦忠成
★目錄:
推薦序
文學對歷史的承諾/ 孫大川
想像多元回憶的神話/ 李弘祺
擦亮後山故事/歷史/ 浦忠成
第一部 奇密花
第二部 苦楝花
序曲
第一幕 白浪
第二幕 商議
第三幕 訂盟
第四幕 凱旋
第五幕 禱告
第六幕 台灣府
第七幕 花蓮港
第八幕 米崙山
第九幕 兩族友情
第十幕 末日前三天
第十一幕 末日前二天
第十二幕 末日前一天
第十三幕 末日之日
第十四幕 逃難
第十五幕 大山
第十六幕 受刑
第十七幕 受難的靈魂
第十八幕 水璉尾
第十九幕 馬立雲
第二十幕 撒固兒
第二十一幕 新社
第二十二幕 化番俚言
第二十三幕 歲月
第二十四幕 水璉李校長
第二十五幕 原來我不是查邦
第二十六幕 火祭
第三部 大庄阿桃
後記
「開山撫番」把兩個台灣變成一個台灣
請訂立「台灣感恩節」
<作者簡介>
陳耀昌 醫師
台灣骨髓移植播種者,「法醫師法」先驅者,幹細胞醫學帶路者(sayum)。榮獲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專業獎章」肯定。六十歲開始寫小說,每出書必獲獎,必為暢銷書。
《福爾摩沙三族記》(遠流)入圍2012文化部「台灣文學獎」
《島嶼DNA》(印刻)2016巫永福文化評論獎
《傀儡花》(印刻)2016文化部「台灣文學獎小說類金典獎」、金石堂2016年度十大影響力好書、2017台北國際書展大獎入圍。公視公司「台灣大河劇」拍攝中。
《獅頭花》獲2017「新台灣和平基金會台灣歷史小說獎」
作者寫歷史小說,均身歷其境踏察,而筆下時帶台灣情。
請讓作者帶領您,去挖掘與探訪被空白,被遺忘的精采台灣歷史,會讓您充滿驚喜及感動。
★內文試閱:
‧推薦序
文學對歷史的承諾
──陳耀昌《苦楝花》序
孫大川
Paelabang danapan
陳耀昌醫師的台灣史花系列三部曲終於完成了。第三部曲《苦楝花Bangas》以花東為場景,敘述1874年至1896年清廷「開山撫番」政策在花蓮、台東推進的情況。一般史書都提及與此相關的三個武裝衝突事件:(一)大港口事件;(二)加禮宛事件;(三)大庄事件。因為台灣原住民各族沒有自己的文字符號系統,毫無疑問的,三大事件的始末幾乎都是以漢人文獻記載為依據,部落族人的聲音是完全聽不到的。這當然不是已陸續完成《傀儡花》和《獅頭花》創作的陳耀昌醫師所能接受的,他必須聽到族人的聲音!陳醫師在本書寫後感言裡,清楚交代了自己在田野調查中見到的人和種種令人驚嘆的巧遇。文學創作的本領,讓他有更大的空間、更大的想像力和自由,去填補文字和文獻無法記錄的聲音,從族人飄渺的口傳記憶裡,讓歷史重新說話。
和以往不同,陳耀昌醫師的《苦楝花》不是用聯貫一氣的長篇小說寫成的,它由兩篇短篇小說和一齣劇本組成。陳醫師最後決定要用這樣的形式來呈現自己台灣史花系列的第三部曲,應該有他的考量;不過,儘管如此,通讀全書之後,細心的讀者仍能在情感上或時間、空間的聯結上,清楚地掌握首尾一致的歷史整體感,這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或許這正是陳醫師嘗試突破的文學筆法之一。
按時間序列,花東「開山撫番」主角吳光亮的出場,是在1877年底1878年初發生的大港口事件。陳耀昌醫師因特殊的理由,認為文獻上記載大港口事件殺戮的主戰場雖然在海岸的「阿棉」、「納納」兩個部落,但「肇因者」卻是深藏在縱谷、海岸之間的「奇密」(今之奇美)部落,文字紀錄淹埋了事實的真相。為突顯原住民部落的主體角色,陳醫師將小說的重心移給了「奇密」。故事用科幻的方式敘述,若干情節和穿越時空的寫作技巧,看起來並不是陳醫師熟悉的手法,有不少破綻和勉強的地方,不過,這可能也是因為他能掌握的口述資料相對貧乏的緣故吧!相反地,寫〈大庒阿桃〉時,陳醫師似乎回到了他熟練的歷史小說寫法,許多情節的安排既合理又讓人驚奇。
整部小說分量最重、最具挑戰性的,當然是以「加禮宛事件」為背景的劇本〈苦楝花〉了。除「序曲」外,全劇總共二十六幕。從主角Kumud Pazik出生開始,一直到撒奇萊雅族正名成功舉行「火祭」,Pazik和妻子卡娜少靈魂甦醒結束,敘述了撒奇萊雅族與吳光亮大戰失敗後一一九年崩解、星散的血淚史。全劇以朗誦的方式閱讀,格外容易引人融入歷史命運的悲涼中。按陳醫師後記的說明,與〈苦楝花〉相關的田野奇遇是最多的,而其關鍵人物是已過世多年的李來旺校長(帝瓦伊•撒耘Tiway Sayum)和他的兩個兒子。藉由他們的帶引,陳醫師得以聽到撒奇萊雅族人的聲音。陳醫師還進一步指出〈苦楝花〉第十幕到第十三幕分別描述「末日前三天」、「末日前二天」、「末日前一天」、「末日之日」頭目Pazik的部分吟誦詞,其實是李來旺校長的祖母Lutuk Sayum口述後,校長記下來的。陳醫師說:「這些文字太神聖了,我將之一字不改運用到書內。」這個聲音,這個撒奇萊雅老人說的話,比文字更有力量!我和李來旺校長是舊識,一九九○年代初,我們曾一同有過愉快的雲南之行。他精通阿美語,有強烈的民族意識,非常會說笑話,每一場演講都能句句扣人心弦。一九九四年他將北富國小正名為「太巴塱國小」,是原住民地名、校名復原的先聲。李校長說:「太巴塱」倒過來唸,漢人會覺得很威風。二○○○年起,我在東華大學任教,我們有了更多相處的機會。二○○三年七月他心肌梗塞的當日清早,我們還一起共餐,延續前一晚說過的笑話,並約好他去為花蓮縣長候選人謝深山站台演講後,再回來東華大學,不料一去竟成永別。他晚年推動撒奇萊雅族正名和文化復振的工作,最後由他的兒子和年輕族人繼續完成。我在閱讀〈苦楝花〉的同時,李校長的影子處處浮現,文學的想像和個人記憶交織、重疊,歷史成了我內在的事。多年前我曾支持台東大學音樂系編排演出了一場大型的原住民歌劇〈逐鹿傳說〉,蔡盛通教授作曲、董恕明教授填詞,這是我們原住民社會比較不習慣的表演形式,頗引起討論。陳耀昌醫師此一〈苦楝花〉劇本,將來若也能以歌劇的方式演出,其張力一定可以造成更具震撼性的效果。
閱讀完陳耀昌醫師整套花系列三部曲,不難發現:從台灣原住民的經驗來看,直到日據時代以前,原住民根本没有國族認同的想像,其認同的邊界僅止於「部落」。後來日本政府雖藉由人類學的方法,完成了原住民族群識別的分類,但跨越「部落」的「族別」認同,依然是極為鬆泛的。這不但可以從霧社事件爆發時,同屬賽德克(Seediq)的德克達雅(Tgdaya)和都達(Toda)不同立場的選擇看出;同時也可以說明2000年後泛泰雅系(Atayal)族群,陸續正名分出泰雅、賽德克和太魯閣(Truku)各族的原因。從這個角度看,習慣於國族敘述的漢人歷史思維,是很難真正理解原住民認同構造的。《傀儡花》、《獅頭花》的歷史場景是如此,《苦楝花》裡各部落的利害關係也是如此。直截了當地說,除非我們打算願意正視原住民的存在,否則荷西、清領、日據到中華民國國族框架下的歷史建構,根本無法反映台灣歷史的本質、真相與全貌。一個根基不穩、偏枯且没有源頭的國史敘述,怎麼可能建立真正的國家主體性?從《福爾摩沙三族記》一路寫下來,陳耀昌醫師的歷史小說創作,似乎一步一步將他帶引到一個愈來愈清楚的結論上,他說:「原漢關係的重要性絶不亞於兩岸關係!」能突破現實政治的重重迷霧以及漢人根深柢固的文化偏見,重新設定台灣歷史的走向,這應該是陳醫師寫作當初,完全没有預想到的結果吧?!是歷史引導了文學?還是文學照亮了歷史?可以肯定的是:「台灣感恩節」的提議,是歷史結合文學引發的心性召喚,也是陳醫師對台灣未來的想像。它的本質是文學的,我雖充滿期待,但因歷史現實的教導,終究不敢太樂觀。
二○一九年六月十日
(本文作者為監察院副院長)
想像多元回憶的神話──閲讀陳耀昌醫師的新作
李弘祺
陳耀昌教授是一個有進步觀念、又有愛心的醫生,他在專業上的成就台灣先趨。陳教授又是一個充滿精力的社會活動家,抱懷上醫治國的理念,行若先知,心越千仞的智者。他又是一位視野廣闊,能右手行醫,左手著述的歷史作家。他不只知交滿天下,不必市義,就可以呼喚市井之民,成就非凡的事功,更能說大人而邈之,取信君子,使鴻儒言計聽從。
所以排隊希望能在陳醫師出書時寫序的人不絕於驛,簡直不可勝計。
也因此,當他找我替他的新書寫序時,我真的是驚喜若狂,即刻答應。因爲我知道如果不馬上承允,那麽一定會很快被他人替代,所以竟然連書稿都沒有看,也不管期限非常短促,急忙中就攬接了下來。
我不用在這裡覆述陳醫師所寫的幾本引人的書的内容。這些書是關心台灣文化以及原民歷史的人必讀之書。他們的重要性就是把一些我們大多數人所忘記的、不重視的、教科書不教的故事用嶄新、有趣的小説体把它們再現到我們的眼前,讓我們在記憶中替它們找到合理的空間,並讓我們深刻地思考,什麽是歷史與文化。作爲一個學歷史的我,這本書中的三次戰役(一八七七年大港口奇密等社的阿眉族人被屠殺事件;一八七八年加禮宛港的撒奇萊雅族被屠殺滅族的戰役;一八八八年的大屠殺戰役),我過去不僅完全不知道,更談不上了解他們的意義。這一次讀了陳醫師感人的小説和史詩般的劇本,我才得到了一個逼真的擬似(virtual)了解。毫無疑問的,最重要的不外就是這些作品使我們看到台灣東部開發過程中所展現的人性光輝,這種光輝在被欺壓詐騙的原住民生活的生命哲學(例如「分享」而不是競爭)中顯得特別的閃爍動人。書中所展現用愛和犧牲來保護為族人的生存和文化是那樣的高尚和純潔更令我每每掩卷而嘆息。不是我同情他們那麽的簡單,而是我感受到爲人的尊嚴就是那麽的切身而真實,那麽的「普世」,是每一個人心中的良知與良能,自然的知識。陳醫師的作品所以引人就正是因爲它是基於同理心,是基於我們都希望回去到那個自然而然的真理,和那個顛撲不破的純真世界。不管是東台灣今天只剩九百人的撒奇萊雅族人,或者是新的東南亞住民,或者是台系漢人。我們都同樣具備有那種高尚和純潔。歷史雖然是自成一格的記憶的反省,但是歷史也是具有共同人性的可以會通的遺產。這就是陳醫師這本書給我的第一個印象。他一系列的作品都在宣示這個信念。
是的,陳醫師的讀者當然不限於那九百個族人。他的讀者是那複雜而卻井然有序的多元台灣,乃至於世界。我記得兩年前的一個下午,我在家裡讀陳醫師的《傀儡花》,正好有一對守望台(Watchtower)的傳教夫婦來訪,我們談到了美國和台灣的種種關係。這對夫婦當然完全沒聼過什麽「荷蘭公主」,更不知道美國與台灣的原民早在一百五十多年前已經締造了外交關係,簽了從美國的立場來看,是一份國際條約。他們驚奇之餘,就問起《傀儡花》有沒有英譯。啊,我何等的希望陳醫師的書能翻譯成爲英文,乃至於其他的外國文字(很高興已經有下村作次郎的日文翻譯,今年九月會出版)!所以,陳醫師的小説是面向世界的,能在多元的文化裡讓人人都激動跳躍的「酵母」(耶穌說:「天國好比酵母,一個婦人拿去拌在三斗麵裡,使得整團麵都發了酵。」)美好的多元文化就是依賴這一個最單純而完美的DNA持續與周遭的生命環境相互交流,從而茁壯的「理一分殊」的生命。用赫德(Johann G. Herder)的話來説,這就像一個英吉利花園:凡爾賽宮的花園固然齊整,但是每五十尺種一棵樹,這個小孩子就可以做到(Alexander Pope語),哪像那個合自然與多元為一的英吉利花園,富麗堂皇乃不足論,豈堪與繁複而美不勝收相比。這不正是用加禮宛故事作爲酵母所帶給我們的反省,帶給我們的認識麽!多元文化是何等美好,又何等壯麗(brave)。
陳醫師的書希望理清記憶和歷史。他用的是記憶:少數人微不足道的經歷和記憶。但是他書寫記憶的背後是要闡述歷史。記憶是小説或史詩(《苦楝花》)的素材:是神話,是沒有經過解釋和反省的傳承。歷史是教育的元素,用來建立國民之間交流的基礎。陳醫師的小説或史詩有神話的特色,「記錄」了很多的故事,甚至於利用所謂「虛構」(更好的話應該是「想像」imagined)的人物來述説沒有過濾的記憶。這樣的作品引人入勝,讓我們知道「what had happened」(發生了什麽事)。但是陳醫師有一個重要的使命,那就是讓這些小説同時得到解釋,好「發明」或「再現」十九世紀的「開山撫番」歷史。顯然地,這個使命是沉重的,而它的展現則是燦爛的。用一句看似簡單的哲學話語來説:「凡發生的就是合理的」(黑格爾的名言)。但是什麽是歷史的理性?陳醫師告訴我們:就是必須經過批判和反省,建構合乎時間長流的目標的知識。大師告訴我們:過去一百多年來的台灣「歷史」其實不是「歷史」,而是「迷思」,是不合理的,連「神話」也不是。因爲「神話」的核心是可以讓人們認同的真理。神話是合理的歷史,而歷史則是人們不斷反省而認同的神話(就好像小説才是真正的歷史一樣)。是的,陳醫師的使命是沉重的,而它卻又是那麽一個難以承受的「輕」(unbearably light)。因此,大師得以遊刃有餘,寫出駕輕就熟的美麗篇章。在台灣史的研究中,陳醫師不僅吸收了當前研究的成果,並且鉅細靡遺地用小説、史詩、戲劇,不,神話,把它們娓娓地細述給我們知道。
陳醫師還有一個小小的心願:那就是在台灣設立「感恩節」,因爲台灣前前後後來到的許多新移民,新台灣人,都欠原住民一個公道。用陳醫師的話來説,這就是:因爲這些後來的移民的誤解或偏見,所以我們不知道,更未能珍惜原住民們的「獨特而與大自然完全結合的文化與價值觀」。這個想法遠遠超過了當年清教徒邀請原住民會餐,以表示感激的簡單「回報」的爲人之道。這是一個文化的宣示,要我們在節日以及在節日之外,必須不斷地反省這塊土地的原始意義:它是獨特的,而又是與自然合一的。許多中國漢人雖然都知道「天人合一」的口號,但是對於自然卻不斷地摧殘,認爲它是中國人面對政治分配不均時,用來補充生活需求的物資來源。現在是重新反省台灣所有族裔所應該有的世界觀和生命價值的時候。我們應該記得我們這個被蔚藍海洋和青翠山林所包圍的自然環境是如何在不斷地呼叫我們回到他的懷抱裏去。「感恩節」是一個共同擁抱文化價值的紀念日,紀念島嶼最原先的DNA所萌發的恢宏胸襟,以及對這塊由原住民首先看護及照顧的大地的誠摯感謝。每一年,我們要再一次聆聽原住民神話的悸動,記住這塊大地所帶給我們大家共同的祝福。
陳醫師是我的學弟,但是他在學術上,寫作上都遠遠超過我的貢獻,我每一拿起他的書,便會覺得人生苦短,會覺得不如沉醉;然而,午夜夢囘,驚聞秋聲,就不能不嚴肅地對待這一切又大師描繪的史詩和歌聲。於是只好暗中嫉妒,認真地寫一篇讀書報告。不足之處,幸無罪我,是所至望。
二○一九年端午之日於台北旅次
(本文作者為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紐約市立大學退休教授)
擦亮後山故事/歷史
浦忠成pasuya poiconx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的《臺灣史》第七章〔清代之治臺〕第七項「撫番諸役」第六目「奇密社之役」:
光緒三年,後山駐軍統領吳光亮,開闢自水尾至大港口道路。附近之奇密社不服,殺總通事林東涯以叛。八月,吳光亮以營官林福喜往彈壓,抵烏鴉立社,中伏潰敗。奇密社番與大港口南岸之納納社番南北相應,勢甚猖獗。乃急調北路統領孫開華率臺北府兵二營;臺灣鎮總兵沈茂勝率臺南府兵一營,及臺灣知縣周懋琦率礮隊,分海陸增援。十二月,援軍齊集,合力進剿。番不支,乞降,許之。
第七目「加禮宛社之役」:
光緒四年正月,商人陳文禮至加禮宛墾田,為番所殺。營官令以金、穀慰死者家屬贖罪,番不聽,且殺傳令兵丁,與竹窩宛社謀叛。是年六月,報聞,以花蓮港營官陳得勝率部伐之,不克。乃請駐臺北府北路統領孫開華來援。吳光亮自駐花蓮港督軍。七月二十六日,討竹窩宛社;翌日,逼加禮宛社,番不支,竄於東角山,會大風雨,多餓死。老番乞降,許之。以酒、布賈其地,東至加禮宛溪,西至山,南至荳蘭,北至加禮宛山。凡荳蘭溪以北為官地,南為番地,各事開墾,勿相侵凌。改加禮宛為佳落,竹窩灣為歸化;番悉服命。
第十一目「臺東之役」:
光緒十四年六月,有大莊(庄)客民劉添旺,委員雷福海者,徵取田畝清丈單費嚴急,民、番胥怨;又拘辱其婦女,眾番忿;遂叛。殺雷福海而毀其屍。襲破水尾房營,殲弁勇,劫掠軍械、火藥而南。七月,糾合呂家望社生番,焚毀臺東直隸州衙門,圍攻駐軍統領張兆連營。……時北洋大臣復派海軍統領丁汝昌以艦來援,艦礮可遠及番社,炸殺甚多,番懼乞降,許之。
這是與陳耀昌醫師「台灣史花系列三部曲」末部《苦楝花》三篇〈奇密花〉、〈苦楝花〕及〈大庄阿桃〉相關而被記載於史書的文字。全然以漢人官方的角度敘述其與阿美族、噶瑪蘭族、撒奇萊雅、大武壠族與馬卡道族之間戰爭的敘事。在這些漢人作者的描述,那些造成部落嚴重傷亡或導致部落瓦解、族人失散甚至族群滅絕、語言文化消失的戰爭,都原始都遭到扭曲,再以輕描淡寫的手筆賦予霸道、栽贓式的歷史注腳:開路,奇密社不服,殺林東涯以叛,番不支,乞降,許之/商人陳文禮至加禮宛墾田,為番所殺。營官令以金、穀慰死者家屬贖罪,番不聽,且殺傳令兵丁,與竹窩宛社謀叛。番悉服命/徵取田畝清丈單費嚴急,民、番胥怨;又拘辱其婦女,眾番忿;遂叛。炸殺甚多,番懼乞降,許之。
開路墾地,侵入別人的領域,或者是強徵苛刻的土地清丈費用,欺負部落婦女,這些事情,凡有血氣人性者遇上,任誰都要義憤填膺!林東涯、陳文禮、雷福海之流,在部落流傳的敘事都是仗勢欺人的惡棍,官府不僅不去懲戒、驅離,還放任其惡行,難怪要引起怨怒。至於如吳光亮等人的集體屠殺、凌遲毒計,以及以艦礮轟擊部落的行徑,有的史書刻意抹消,所幸當年自劫難逃脫者的敘述的口碑依然傳續,可以核對漢文紀錄的真偽。
陳耀昌醫師在《苦楝花》敘寫的故事,就是由歷史地點的踏查、相關人物的訪問逐漸形成的敘事架構。陳耀昌醫師以三種截然不同的寫作模式完成三篇不同歷史的表述。〈奇密花〉以一個現代女性研究者在偶然的夢境回返/進入大港口事件中吳光亮設計屠殺阿美族人的現場,在參與/陪伴/窺視的情境中,親睹/再現流傳在阿美族部落的自主敘事。〈苦楝花〉作者自言是模仿莎翁劇作的筆法,藉由噶瑪蘭族加禮宛社及撒奇萊雅族達固部灣社領袖(頭目)、青年領導者等的對話、情勢演進的敘說,以二十六幕呈現噶瑪蘭、撒奇萊雅兩族對抗清軍以至敗陣、逃離、失散百多年後,終於再凝聚的歷程。詩行排列的白話文辭,卻能有凝鍊、緊湊的表意效果。〈大庄阿桃〉以一個女性的角度觀看部落以及族人(尤其是男性)如何面對清代官軍的跋扈與地方官吏的醜惡行徑。再去看看局勢改變後,原本魚肉族人的清朝官兵們在遭部落戰士與日軍追殺時的狼狽。她的牽手阿勇也跟著部落的男人一起襲擊清軍兵營、官署,卻沒能保命回來。後來靠著項鍊,阿桃知道了阿勇最後的結局,也因為它而讓她願意收容離鄉背井的湘軍落地生根。〈大庄阿桃〉敘說自西部翻山越嶺來到東部縱谷尋找新居地的平埔族群如何想辦法生存的故事,在在展現女性的堅強與包容能量。
陳耀昌醫師靠著精準的觀察,以及他自言的好運氣,完整彙集了這些史事的部落觀點與在地說法。他確實也找到、遇到了跟這些史事具有關鍵意義的人物,得以更好佐證他故事/歷史的信實。所幸陳耀昌醫師的努力尋訪,讓這些故事/歷史再次被擦亮。奇美/奇密部落現在成為秀姑巒溪泛舟途中的休息點,南邊的靜埔與北邊港口部落,也是東海岸旅行者熟知的地方。達固部灣、馬立雲、加禮宛、新社等在撒奇萊雅與噶瑪蘭族陸續正名後逐漸為人所知悉。大庄/東里隱藏的故事在《苦楝花》中也被揭露了。陳耀昌醫師這本《苦楝花》應該可以讓行遊東部縱谷與東海岸的旅人得以增添更多歷史/故事探索的興味。有此榮幸得以先讀,謹以感謝、感動的心情作此序文。
二○一九年六月六日寫於壽豐
(本文作者為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院長)
‧摘文
第一部 奇密花
朱小君一天之中兩次得到旅遊的邀約,真是心花怒放。
上午,她在研究室,她的碩士論文指導老師在接了一個很長的電話後,告訴她:「一位廣東著名大學的歷史系教授來電,明年要在吳光亮的生日,在吳光亮故鄉舉辦一個吳光亮研討會。如果妳確定妳的研究題目是花蓮開發史,吳光亮是一個重要的人物,妳考慮一下要不要去。」接著又自言自語地說:「奇怪,吳光亮是一八三四年生的,明年二○二○,吳光亮一八六歲,不是二百周年也不是一五○周年……」
她知道吳光亮。唸台灣史的研究生無人不知吳光亮。一八七四年沈葆楨開山撫番,是台灣史的里程碑。開山,就是闢了三條山路,貫穿大山,到達以前難以到達的後山。這三位將領北路羅大春,中路吳光亮,南路張其光,從此名留台灣史。中路大約就是現在的「八通關古道」,由竹山(舊名林圮埔)到花蓮玉里(舊名璞石閣)。
八通關古道現在仍是許多登山者之上選路徑。但除了這個,有關吳光亮,她知道的就不多了。
好巧,當天晚上,她和男友吃飯,男友說,要給她一個可以永遠回憶的生日禮物──到秀姑巒溪去泛舟。男友興沖沖告訴她行程的安排:先到玉里過一夜,第二天早上搭火車到瑞穗。午飯後泛舟,大約一點半開始,自瑞穗大橋到秀姑巒溪出口長虹大橋。河段二十二公里,航程三至四小時。然後晚上在靜浦當地找一家民宿住,第三天早上去花蓮,再遊太魯閣。
她高興極了,拋了一個飛吻給男友表示滿意。男友是玉里人,兩人都在台中唸大學。她去年考上了歷史碩士班,男友則是另一所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住院醫師。交往近一年,她還沒到過男友家,也沒有去過玉里。她心中暗喜,她男友似有帶她見公婆的意思。
她完全未曾來過花東。她決定以花蓮的開發史為研究論文,只因為男友是花蓮玉里人。她本身是彰化人,對東部完全陌生。
男友聽到她明年要到「吳光亮研討會」,很高興地說:「那太巧了,我們玉里有一所大廟,和吳光亮兄弟好像頗有淵源呢!」
「我早知道啦。你們玉里是當年開山撫番中路,八通關古道的終點呢!有吳光亮的一些遺址是必然的。他弟弟叫吳光忠,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之戰時仍戍守東港,準備抗拒日軍。胡適的老爸胡鐵花在日記中也提到他。呵呵,我台灣史可不是唸假的!」男朋友作勢向她敬了一個禮。
老師既然要帶她去,不會沒有工作分配下來。於是她上網買了一本《吳光亮傳》,是台灣省文獻會一九九四年出版的,屬於「台灣先賢先烈專輯」,作者是一位文獻會約聘研究員。
這大概是台灣最詳盡的有關吳光亮的記述了。作者是竹山人,竹山正是「八通關古道起點」。小君不禁啞然失笑,真巧。這位作者因成長於八通關古道起點,而對吳光亮有興趣;她因男友成長於八通關終點而對吳光亮有興趣。這本《吳光亮傳》她匆匆讀過,她印象最深的是吳光亮光緒元年開通八通關古道,後來在光緒三年,有個「納納、阿棉事件」;光緒四年,又有個「加禮宛社事件」。
「加禮宛事件」她略有所聞,「阿棉社事件」則不太清楚。看了《吳光亮傳》的描述,又找了地圖(見夏獻綸之「台灣後山全圖」)來看,才有一些概念。光緒三年,吳光亮在璞石閣立了大營,然後要開闢水尾到大港口的道路。沿路阿棉、納納兩社不願,於是與吳光亮打了幾場仗,各有勝負。後來吳光亮一仗殺了一百四十位原住民,終於獲勝。而且光緒四年春三月七日,清廷以攻克阿棉、納納兩社「兇番」,賞台灣道夏獻綸封典、優敍,吳光亮與孫開華等黃馬掛,寬免副將林福喜等處分,並予陣亡都司羅魁優卹。這是她模模糊糊的了解。
吳光亮在那二個「討伐」事件後,寫了「化番俚言」,共三十二句,每句八個字,代表了那時漢人對番人為「蠻夷」、「缺乏教化」的看法。
她嘆了一口氣。這本《吳光亮傳》就是完全漢人中心觀點,對吳光亮全部正面描述,歌功頌德。也難怪,二十年前的書了。而台灣現在已經不一樣了,漢人已知道反省,原漢漸漸往平權邁進中。
後來她又買了一本吳光亮的奏章集,也是文獻會出版的「吳光祿使閩奏稿選錄」,都是一些文言文奏章,看了大失所望,沒有去唸。
※
小君和男友先搭高鐵自台中到左營,再轉台鐵,由左營到屏東。到了枋寮,小君不覺精神一振。這就進入一八七四年牡丹社事件時所謂「瑯嶠」,或一八七五年「開山撫番」以後的恆春縣地域了。火車經過加祿站、內獅站,小君更興奮,她讀過陳耀昌的《獅頭花》,知道這裡是當年大龜文部落酋邦內獅、外獅部落大戰清國淮軍之處。那是開山撫番後第一個原住民與清國官兵的戰爭。
火車進入大武山區,這是當年大龜文的心臟地區,風景絕美。小君和男友心情好High。車到大武,終於到了台灣的東海岸。火車沿著太平洋走,山勢、海景更是令人如醉如痴。過了知本之後,火車進入台東及花蓮的縱谷。荷蘭人、漢人進入東部「後山」,大抵就是這樣走的,先到台東,再到花蓮。一開始全稱為「台東州」,後來把卑南大溪流域稱為「台東」,把秀姑巒溪流域分出為「花蓮」。當年花蓮是台東州的一部分,但現在卻稱為「花東」,而非「東花」了,小君想。
車過台東,開始進入卑南大溪流域。她以前沒想到卑南大溪如此雄偉,縱谷又如此秀麗。過了卑南大溪流域,進入花蓮境內的秀姑巒溪流域後,第一個大站就是玉里。現在一般台灣人聽到玉里,大概只知道這裡有個大型的老兵醫院或養老中心,而完全不了解玉里在台灣開拓史的地位。連她男友都不知玉里舊名「璞石閣」,小君嘆息著。這也是她論文選擇「東部開發」為題目的原意,「其實我也是多知道一點點而已。」她想。
男友的父母,顯然對小君印象不錯,在晚飯時與她談了許多花蓮的美景與物產。他們很好奇小君為什麼唸歷史,問小君說,唸歷史除了當國中、高中老師以外,還可以有什麼職業?男友搶著回答說,當國中老師一年有三個月寒暑假,有什麼不好?!小君笑笑,沒有說些什麼,但其實心中有些不滿,她想,豈可如此小看唸歷史的。
第二天早上,小君和男友到了「協天宮」。這協天宮,以玉里小鎮的規模,可算是金碧輝煌的大廟。當年吳光亮在光緒元年開通了現在稱為「八通關古道」到璞石閣,第二年就立了這個廟,大概是在花東最有歷史意義的大廟了。那有名的「後山屏障」的匾額,掛得很高,加上歲月洗禮及焚香煙薰,綠底金字,小君看得吃力,也無法辨出題款的字。反而是她查了Google,知道這匾是光緒七年立的。「所以是那些事件以後才立的了」,小君想。
協天宮的廟埕立有一塊石碑,小君一字一字唸出碑文,邊唸邊笑出聲。
……西元一八七五年,運會所趨,交通首要,八通古道,迫於修建,自林圮埔至花蓮樸石閣(今玉里),通衢以來,吳氏昆仲,光亮光忠,率飛虎左營前駐,安屯之後,天意難料,瘟疫大行,手足惶錯,素仰帝君,仁義禮智,三界伏魔,爰築草屋,吳光亮將軍親題,後山保障匾額,以奉祀迄今。後山居民,族群龐雜,阿美布農,平埔客家,漢民雜處,嫌隙難免,爭端時起,幸賴神召,和諧共居。……
男友在旁邊補充著:「是啊,我們這裡的血統很複雜,高山原住民有布農、阿美,平地在閩、客之外,還有許多西部的平埔西拉雅或馬卡道,在十八、十九世紀因被漢人壓迫而越過中央山脈,遷徙到此。我本人是客家,我們祖先是清朝光緒年間過來的,雖然才短短五、六代,我懷疑我說不定也有平埔血統呢。」
對台灣史較熟稔的小君說:「你們這裡的平埔,是自台南頭社或玉井一帶遷來的。他們認為自己是大武壠或大滿,與西拉雅有些不同。另外有些是由屏東林邊放索、萬丹一帶,經由浸水營古道遷來,他們則認為自己是馬卡道,不是西拉雅,也不是大武壠。你們家混的,是大武壠還是馬卡道?」
男友苦笑道:「妳問我,我問誰啊?」又問:「妳剛剛為什麼一直笑,在笑什麼?」
「好啦,」小君笑道:「其實我是笑這碑文的文字,道盡漢人的偽善與假仁假義。我們唸歷史的,都知道吳光亮在後山,殺了不少原住民,但他卻頒布了〈化番俚言〉,好像他只強調感化,從不殺戮似的。過去漢人統治者一貫如此,滿口仁義道德,作為凶狠毒辣。這也許就是原住民一直不喜歡漢人,不信任漢人的原因吧。」
小君又說:「例如剛剛大殿那個『後山保障』,大家認為吳光忠所題的匾,又是另外一個例子。『後山保障』,保障了誰啊?後山本來是原住民的,難道是吳光亮保障了原住民嗎?恰恰相反,是保障了入侵後山的漢人啊!。」男友在一旁苦笑著。
小君看到表情尷尬的男友:「唉,現在是多元共榮啦,也沒要你們漢人搬出後山,只是要你們不要繼續這一付道貌岸然,滿口道德的漢人沙文主義觀點就是。」又說:「高中課本決定不採用連橫的《台灣通史序》,就是因為原住民詩人莫那能的一句話:『你們的篳路藍縷,我們的顛沛流離!』」
男友打哈哈說:「只道你們這些唸歷史的最冬烘,誰知反而思想最前衛,最進步了。佩服佩服。」
小君說:「唸歷史是為了反省,以史為鏡,說的就是這個。你們學醫的,醫人醫獸;我們學歷史的,醫國家醫社會,作用大著呢,豈是為了三個月寒暑假。」
男友說:「哎呀,失敬失敬。我必須多了解一些台灣史了。」
小君笑說:「那還用說!」但又感慨。她說:「其實,在台灣史方面,我們過去承緒了太多漢人史觀,都是一面之詞,因此要好好重新評估。許多歷史事件,原住民的觀點沒有能留下來,因而真相不太清楚。例如這位吳光亮,在〈化番俚言〉卷首,又加了一篇光緒五年(一八七九)『諭後山各路番眾』的曉諭,也說得冠冕堂皇。先舉前幾年阿棉、納納、加禮宛等社,經吳光亮『親統大軍,嚴加痛剿,以張天威』,然後經過設立番學,教番童識字讀書,最後以這三十二條『淺近野俚』的《化番俚言》,而使『蠻夷僻陋之俗,轉成禮義廉讓之風』。」
小君有著感概。加禮宛事件她略知一二,但阿棉、納納的地名今已不存,因此不知詳情。但總之,這就是台灣原住民的「被漢化過程」,當然包括日常風俗的改漢姓、穿漢服…等,把「漢化」當「教化」。小君感慨著,這就是過去不尊重少數族群的漢人沙文主義及擴張主義,自以為是的偏見。
一直要到這幾年,台灣社會才慢慢了解原住民文化有其融自然天地於一體的優點。在過去漢人讚美「人定勝天」、「愚公移山」、「戰勝大自然」的時候,漢人看不到原住民優點,認為原住民懶散、笨拙,只會唱歌跳舞。要等近幾年屢屢出現大自然的反撲之後,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住民文化比我們看得更遠……。其實日本人早看出了這一點。森丑之助說,站到山上,青翠的地方就是番人的,光禿禿的地方就是漢人的。這正是現代才有的「水土保持」的生態思維。而當年,則視為原民之疏懶。在一九二五年之前,森丑之助就看出了原住民文化的優越,但他也無法勸服那個年代的日本總督府,所以他只好在基隆港跳海…。
在火車到瑞穗的途中,小君一路上讚嘆著窗外花東縱谷的秀麗景色。她的男友,則臉色有點臭,帶女友來旅行,女友則沒有柔情蜜意,而卻鍾情於歷史和原住民,還一路上談歪理,倒有些像是在譴責他。
苦楝花Banga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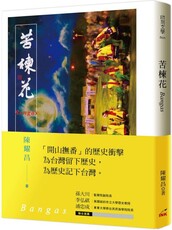
 苦楝花Bangas
苦楝花Bangas作者:陳耀昌 出版社:印刻 出版日期:2019-06-28 00:00:00
<內容簡介>
「開山撫番」的歷史衝擊!
為台灣留下歷史,為歷史記下台灣
三個後山原住民族「被開山撫番」的故事。
陳耀昌賦予原住民的角度與感受。
〈奇密花〉
她不自覺地流下眼淚來。這個操場就是整整一百四十一年前,吳光亮屠殺原住民的地方,現在稱為「大港口事件」的發生地。而其實,大港口事件只是眾多戰役及大屠殺的一節。她回到操場邊,昨夜的槍聲及慘叫聲又在他腦中響起。她跪了下來,向埋在地下的亡靈表示歉意。
〈苦楝花〉(撒奇萊雅語Bangas)
撒奇萊雅的故事,從來沒有戰爭。撒奇萊雅的故事,頂多只有喜歡嚇人的巨人阿里嘎該。撒奇萊雅的故事,頂多是會欺騙小孩的的阿里嘎該。撒奇萊雅的地域從未有戰爭,撒奇萊雅不要戰爭。木神Sakul啊,撒奇萊雅不要戰爭,但是白浪敵人一直侵凌加禮宛及撒族。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所以撒族過去從未有戰爭。人既犯我撒族,撒族抵抗有錯嗎?
〈大庄阿桃〉
萬一像加禮宛的事也發生在我們大庄,Taiovan族的歷史必須永遠流傳下去。所以我希望大家保持警覺。每一家都必須準備一些食物,如果官兵真的來了,我們必須到山中去躲一陣子。
★本書特色:
繼《傀儡花》《獅頭花》之後,「台灣三部曲」最後一部《苦楝花》重磅上市!
★名人推薦:
孫大川│監察院副院長
李弘祺│美國紐約市立大學歷史教授
浦忠成│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院長
──聯合推薦
陳醫師在本書寫後感言裡,清楚交代了自己在田野調查中見到的人和種種令人驚嘆的巧遇。文學創作的本領,讓他有更大的空間、更大的想像力和自由,去填補文字和文獻無法記錄的聲音,從族人飄渺的口傳記憶裡,讓歷史重新說話。──孫大川
陳醫師有一個重要的使命,那就是讓這些小説同時得到解釋,好「發明」或「再現」十九世紀的「開山撫番」歷史。顯然地,這個使命是沉重的,而它的展現則是燦爛的。──李弘祺
陳耀昌醫師的努力尋訪,讓這些故事/歷史再次被擦亮。這本《苦楝花》應該可以讓行遊東部縱谷與東海岸的旅人得以增添更多歷史/故事探索的興味。──浦忠成
★目錄:
推薦序
文學對歷史的承諾/ 孫大川
想像多元回憶的神話/ 李弘祺
擦亮後山故事/歷史/ 浦忠成
第一部 奇密花
第二部 苦楝花
序曲
第一幕 白浪
第二幕 商議
第三幕 訂盟
第四幕 凱旋
第五幕 禱告
第六幕 台灣府
第七幕 花蓮港
第八幕 米崙山
第九幕 兩族友情
第十幕 末日前三天
第十一幕 末日前二天
第十二幕 末日前一天
第十三幕 末日之日
第十四幕 逃難
第十五幕 大山
第十六幕 受刑
第十七幕 受難的靈魂
第十八幕 水璉尾
第十九幕 馬立雲
第二十幕 撒固兒
第二十一幕 新社
第二十二幕 化番俚言
第二十三幕 歲月
第二十四幕 水璉李校長
第二十五幕 原來我不是查邦
第二十六幕 火祭
第三部 大庄阿桃
後記
「開山撫番」把兩個台灣變成一個台灣
請訂立「台灣感恩節」
<作者簡介>
陳耀昌 醫師
台灣骨髓移植播種者,「法醫師法」先驅者,幹細胞醫學帶路者(sayum)。榮獲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專業獎章」肯定。六十歲開始寫小說,每出書必獲獎,必為暢銷書。
《福爾摩沙三族記》(遠流)入圍2012文化部「台灣文學獎」
《島嶼DNA》(印刻)2016巫永福文化評論獎
《傀儡花》(印刻)2016文化部「台灣文學獎小說類金典獎」、金石堂2016年度十大影響力好書、2017台北國際書展大獎入圍。公視公司「台灣大河劇」拍攝中。
《獅頭花》獲2017「新台灣和平基金會台灣歷史小說獎」
作者寫歷史小說,均身歷其境踏察,而筆下時帶台灣情。
請讓作者帶領您,去挖掘與探訪被空白,被遺忘的精采台灣歷史,會讓您充滿驚喜及感動。
★內文試閱:
‧推薦序
文學對歷史的承諾
──陳耀昌《苦楝花》序
孫大川
Paelabang danapan
陳耀昌醫師的台灣史花系列三部曲終於完成了。第三部曲《苦楝花Bangas》以花東為場景,敘述1874年至1896年清廷「開山撫番」政策在花蓮、台東推進的情況。一般史書都提及與此相關的三個武裝衝突事件:(一)大港口事件;(二)加禮宛事件;(三)大庄事件。因為台灣原住民各族沒有自己的文字符號系統,毫無疑問的,三大事件的始末幾乎都是以漢人文獻記載為依據,部落族人的聲音是完全聽不到的。這當然不是已陸續完成《傀儡花》和《獅頭花》創作的陳耀昌醫師所能接受的,他必須聽到族人的聲音!陳醫師在本書寫後感言裡,清楚交代了自己在田野調查中見到的人和種種令人驚嘆的巧遇。文學創作的本領,讓他有更大的空間、更大的想像力和自由,去填補文字和文獻無法記錄的聲音,從族人飄渺的口傳記憶裡,讓歷史重新說話。
和以往不同,陳耀昌醫師的《苦楝花》不是用聯貫一氣的長篇小說寫成的,它由兩篇短篇小說和一齣劇本組成。陳醫師最後決定要用這樣的形式來呈現自己台灣史花系列的第三部曲,應該有他的考量;不過,儘管如此,通讀全書之後,細心的讀者仍能在情感上或時間、空間的聯結上,清楚地掌握首尾一致的歷史整體感,這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或許這正是陳醫師嘗試突破的文學筆法之一。
按時間序列,花東「開山撫番」主角吳光亮的出場,是在1877年底1878年初發生的大港口事件。陳耀昌醫師因特殊的理由,認為文獻上記載大港口事件殺戮的主戰場雖然在海岸的「阿棉」、「納納」兩個部落,但「肇因者」卻是深藏在縱谷、海岸之間的「奇密」(今之奇美)部落,文字紀錄淹埋了事實的真相。為突顯原住民部落的主體角色,陳醫師將小說的重心移給了「奇密」。故事用科幻的方式敘述,若干情節和穿越時空的寫作技巧,看起來並不是陳醫師熟悉的手法,有不少破綻和勉強的地方,不過,這可能也是因為他能掌握的口述資料相對貧乏的緣故吧!相反地,寫〈大庒阿桃〉時,陳醫師似乎回到了他熟練的歷史小說寫法,許多情節的安排既合理又讓人驚奇。
整部小說分量最重、最具挑戰性的,當然是以「加禮宛事件」為背景的劇本〈苦楝花〉了。除「序曲」外,全劇總共二十六幕。從主角Kumud Pazik出生開始,一直到撒奇萊雅族正名成功舉行「火祭」,Pazik和妻子卡娜少靈魂甦醒結束,敘述了撒奇萊雅族與吳光亮大戰失敗後一一九年崩解、星散的血淚史。全劇以朗誦的方式閱讀,格外容易引人融入歷史命運的悲涼中。按陳醫師後記的說明,與〈苦楝花〉相關的田野奇遇是最多的,而其關鍵人物是已過世多年的李來旺校長(帝瓦伊•撒耘Tiway Sayum)和他的兩個兒子。藉由他們的帶引,陳醫師得以聽到撒奇萊雅族人的聲音。陳醫師還進一步指出〈苦楝花〉第十幕到第十三幕分別描述「末日前三天」、「末日前二天」、「末日前一天」、「末日之日」頭目Pazik的部分吟誦詞,其實是李來旺校長的祖母Lutuk Sayum口述後,校長記下來的。陳醫師說:「這些文字太神聖了,我將之一字不改運用到書內。」這個聲音,這個撒奇萊雅老人說的話,比文字更有力量!我和李來旺校長是舊識,一九九○年代初,我們曾一同有過愉快的雲南之行。他精通阿美語,有強烈的民族意識,非常會說笑話,每一場演講都能句句扣人心弦。一九九四年他將北富國小正名為「太巴塱國小」,是原住民地名、校名復原的先聲。李校長說:「太巴塱」倒過來唸,漢人會覺得很威風。二○○○年起,我在東華大學任教,我們有了更多相處的機會。二○○三年七月他心肌梗塞的當日清早,我們還一起共餐,延續前一晚說過的笑話,並約好他去為花蓮縣長候選人謝深山站台演講後,再回來東華大學,不料一去竟成永別。他晚年推動撒奇萊雅族正名和文化復振的工作,最後由他的兒子和年輕族人繼續完成。我在閱讀〈苦楝花〉的同時,李校長的影子處處浮現,文學的想像和個人記憶交織、重疊,歷史成了我內在的事。多年前我曾支持台東大學音樂系編排演出了一場大型的原住民歌劇〈逐鹿傳說〉,蔡盛通教授作曲、董恕明教授填詞,這是我們原住民社會比較不習慣的表演形式,頗引起討論。陳耀昌醫師此一〈苦楝花〉劇本,將來若也能以歌劇的方式演出,其張力一定可以造成更具震撼性的效果。
閱讀完陳耀昌醫師整套花系列三部曲,不難發現:從台灣原住民的經驗來看,直到日據時代以前,原住民根本没有國族認同的想像,其認同的邊界僅止於「部落」。後來日本政府雖藉由人類學的方法,完成了原住民族群識別的分類,但跨越「部落」的「族別」認同,依然是極為鬆泛的。這不但可以從霧社事件爆發時,同屬賽德克(Seediq)的德克達雅(Tgdaya)和都達(Toda)不同立場的選擇看出;同時也可以說明2000年後泛泰雅系(Atayal)族群,陸續正名分出泰雅、賽德克和太魯閣(Truku)各族的原因。從這個角度看,習慣於國族敘述的漢人歷史思維,是很難真正理解原住民認同構造的。《傀儡花》、《獅頭花》的歷史場景是如此,《苦楝花》裡各部落的利害關係也是如此。直截了當地說,除非我們打算願意正視原住民的存在,否則荷西、清領、日據到中華民國國族框架下的歷史建構,根本無法反映台灣歷史的本質、真相與全貌。一個根基不穩、偏枯且没有源頭的國史敘述,怎麼可能建立真正的國家主體性?從《福爾摩沙三族記》一路寫下來,陳耀昌醫師的歷史小說創作,似乎一步一步將他帶引到一個愈來愈清楚的結論上,他說:「原漢關係的重要性絶不亞於兩岸關係!」能突破現實政治的重重迷霧以及漢人根深柢固的文化偏見,重新設定台灣歷史的走向,這應該是陳醫師寫作當初,完全没有預想到的結果吧?!是歷史引導了文學?還是文學照亮了歷史?可以肯定的是:「台灣感恩節」的提議,是歷史結合文學引發的心性召喚,也是陳醫師對台灣未來的想像。它的本質是文學的,我雖充滿期待,但因歷史現實的教導,終究不敢太樂觀。
二○一九年六月十日
(本文作者為監察院副院長)
想像多元回憶的神話──閲讀陳耀昌醫師的新作
李弘祺
陳耀昌教授是一個有進步觀念、又有愛心的醫生,他在專業上的成就台灣先趨。陳教授又是一個充滿精力的社會活動家,抱懷上醫治國的理念,行若先知,心越千仞的智者。他又是一位視野廣闊,能右手行醫,左手著述的歷史作家。他不只知交滿天下,不必市義,就可以呼喚市井之民,成就非凡的事功,更能說大人而邈之,取信君子,使鴻儒言計聽從。
所以排隊希望能在陳醫師出書時寫序的人不絕於驛,簡直不可勝計。
也因此,當他找我替他的新書寫序時,我真的是驚喜若狂,即刻答應。因爲我知道如果不馬上承允,那麽一定會很快被他人替代,所以竟然連書稿都沒有看,也不管期限非常短促,急忙中就攬接了下來。
我不用在這裡覆述陳醫師所寫的幾本引人的書的内容。這些書是關心台灣文化以及原民歷史的人必讀之書。他們的重要性就是把一些我們大多數人所忘記的、不重視的、教科書不教的故事用嶄新、有趣的小説体把它們再現到我們的眼前,讓我們在記憶中替它們找到合理的空間,並讓我們深刻地思考,什麽是歷史與文化。作爲一個學歷史的我,這本書中的三次戰役(一八七七年大港口奇密等社的阿眉族人被屠殺事件;一八七八年加禮宛港的撒奇萊雅族被屠殺滅族的戰役;一八八八年的大屠殺戰役),我過去不僅完全不知道,更談不上了解他們的意義。這一次讀了陳醫師感人的小説和史詩般的劇本,我才得到了一個逼真的擬似(virtual)了解。毫無疑問的,最重要的不外就是這些作品使我們看到台灣東部開發過程中所展現的人性光輝,這種光輝在被欺壓詐騙的原住民生活的生命哲學(例如「分享」而不是競爭)中顯得特別的閃爍動人。書中所展現用愛和犧牲來保護為族人的生存和文化是那樣的高尚和純潔更令我每每掩卷而嘆息。不是我同情他們那麽的簡單,而是我感受到爲人的尊嚴就是那麽的切身而真實,那麽的「普世」,是每一個人心中的良知與良能,自然的知識。陳醫師的作品所以引人就正是因爲它是基於同理心,是基於我們都希望回去到那個自然而然的真理,和那個顛撲不破的純真世界。不管是東台灣今天只剩九百人的撒奇萊雅族人,或者是新的東南亞住民,或者是台系漢人。我們都同樣具備有那種高尚和純潔。歷史雖然是自成一格的記憶的反省,但是歷史也是具有共同人性的可以會通的遺產。這就是陳醫師這本書給我的第一個印象。他一系列的作品都在宣示這個信念。
是的,陳醫師的讀者當然不限於那九百個族人。他的讀者是那複雜而卻井然有序的多元台灣,乃至於世界。我記得兩年前的一個下午,我在家裡讀陳醫師的《傀儡花》,正好有一對守望台(Watchtower)的傳教夫婦來訪,我們談到了美國和台灣的種種關係。這對夫婦當然完全沒聼過什麽「荷蘭公主」,更不知道美國與台灣的原民早在一百五十多年前已經締造了外交關係,簽了從美國的立場來看,是一份國際條約。他們驚奇之餘,就問起《傀儡花》有沒有英譯。啊,我何等的希望陳醫師的書能翻譯成爲英文,乃至於其他的外國文字(很高興已經有下村作次郎的日文翻譯,今年九月會出版)!所以,陳醫師的小説是面向世界的,能在多元的文化裡讓人人都激動跳躍的「酵母」(耶穌說:「天國好比酵母,一個婦人拿去拌在三斗麵裡,使得整團麵都發了酵。」)美好的多元文化就是依賴這一個最單純而完美的DNA持續與周遭的生命環境相互交流,從而茁壯的「理一分殊」的生命。用赫德(Johann G. Herder)的話來説,這就像一個英吉利花園:凡爾賽宮的花園固然齊整,但是每五十尺種一棵樹,這個小孩子就可以做到(Alexander Pope語),哪像那個合自然與多元為一的英吉利花園,富麗堂皇乃不足論,豈堪與繁複而美不勝收相比。這不正是用加禮宛故事作爲酵母所帶給我們的反省,帶給我們的認識麽!多元文化是何等美好,又何等壯麗(brave)。
陳醫師的書希望理清記憶和歷史。他用的是記憶:少數人微不足道的經歷和記憶。但是他書寫記憶的背後是要闡述歷史。記憶是小説或史詩(《苦楝花》)的素材:是神話,是沒有經過解釋和反省的傳承。歷史是教育的元素,用來建立國民之間交流的基礎。陳醫師的小説或史詩有神話的特色,「記錄」了很多的故事,甚至於利用所謂「虛構」(更好的話應該是「想像」imagined)的人物來述説沒有過濾的記憶。這樣的作品引人入勝,讓我們知道「what had happened」(發生了什麽事)。但是陳醫師有一個重要的使命,那就是讓這些小説同時得到解釋,好「發明」或「再現」十九世紀的「開山撫番」歷史。顯然地,這個使命是沉重的,而它的展現則是燦爛的。用一句看似簡單的哲學話語來説:「凡發生的就是合理的」(黑格爾的名言)。但是什麽是歷史的理性?陳醫師告訴我們:就是必須經過批判和反省,建構合乎時間長流的目標的知識。大師告訴我們:過去一百多年來的台灣「歷史」其實不是「歷史」,而是「迷思」,是不合理的,連「神話」也不是。因爲「神話」的核心是可以讓人們認同的真理。神話是合理的歷史,而歷史則是人們不斷反省而認同的神話(就好像小説才是真正的歷史一樣)。是的,陳醫師的使命是沉重的,而它卻又是那麽一個難以承受的「輕」(unbearably light)。因此,大師得以遊刃有餘,寫出駕輕就熟的美麗篇章。在台灣史的研究中,陳醫師不僅吸收了當前研究的成果,並且鉅細靡遺地用小説、史詩、戲劇,不,神話,把它們娓娓地細述給我們知道。
陳醫師還有一個小小的心願:那就是在台灣設立「感恩節」,因爲台灣前前後後來到的許多新移民,新台灣人,都欠原住民一個公道。用陳醫師的話來説,這就是:因爲這些後來的移民的誤解或偏見,所以我們不知道,更未能珍惜原住民們的「獨特而與大自然完全結合的文化與價值觀」。這個想法遠遠超過了當年清教徒邀請原住民會餐,以表示感激的簡單「回報」的爲人之道。這是一個文化的宣示,要我們在節日以及在節日之外,必須不斷地反省這塊土地的原始意義:它是獨特的,而又是與自然合一的。許多中國漢人雖然都知道「天人合一」的口號,但是對於自然卻不斷地摧殘,認爲它是中國人面對政治分配不均時,用來補充生活需求的物資來源。現在是重新反省台灣所有族裔所應該有的世界觀和生命價值的時候。我們應該記得我們這個被蔚藍海洋和青翠山林所包圍的自然環境是如何在不斷地呼叫我們回到他的懷抱裏去。「感恩節」是一個共同擁抱文化價值的紀念日,紀念島嶼最原先的DNA所萌發的恢宏胸襟,以及對這塊由原住民首先看護及照顧的大地的誠摯感謝。每一年,我們要再一次聆聽原住民神話的悸動,記住這塊大地所帶給我們大家共同的祝福。
陳醫師是我的學弟,但是他在學術上,寫作上都遠遠超過我的貢獻,我每一拿起他的書,便會覺得人生苦短,會覺得不如沉醉;然而,午夜夢囘,驚聞秋聲,就不能不嚴肅地對待這一切又大師描繪的史詩和歌聲。於是只好暗中嫉妒,認真地寫一篇讀書報告。不足之處,幸無罪我,是所至望。
二○一九年端午之日於台北旅次
(本文作者為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紐約市立大學退休教授)
擦亮後山故事/歷史
浦忠成pasuya poiconx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的《臺灣史》第七章〔清代之治臺〕第七項「撫番諸役」第六目「奇密社之役」:
光緒三年,後山駐軍統領吳光亮,開闢自水尾至大港口道路。附近之奇密社不服,殺總通事林東涯以叛。八月,吳光亮以營官林福喜往彈壓,抵烏鴉立社,中伏潰敗。奇密社番與大港口南岸之納納社番南北相應,勢甚猖獗。乃急調北路統領孫開華率臺北府兵二營;臺灣鎮總兵沈茂勝率臺南府兵一營,及臺灣知縣周懋琦率礮隊,分海陸增援。十二月,援軍齊集,合力進剿。番不支,乞降,許之。
第七目「加禮宛社之役」:
光緒四年正月,商人陳文禮至加禮宛墾田,為番所殺。營官令以金、穀慰死者家屬贖罪,番不聽,且殺傳令兵丁,與竹窩宛社謀叛。是年六月,報聞,以花蓮港營官陳得勝率部伐之,不克。乃請駐臺北府北路統領孫開華來援。吳光亮自駐花蓮港督軍。七月二十六日,討竹窩宛社;翌日,逼加禮宛社,番不支,竄於東角山,會大風雨,多餓死。老番乞降,許之。以酒、布賈其地,東至加禮宛溪,西至山,南至荳蘭,北至加禮宛山。凡荳蘭溪以北為官地,南為番地,各事開墾,勿相侵凌。改加禮宛為佳落,竹窩灣為歸化;番悉服命。
第十一目「臺東之役」:
光緒十四年六月,有大莊(庄)客民劉添旺,委員雷福海者,徵取田畝清丈單費嚴急,民、番胥怨;又拘辱其婦女,眾番忿;遂叛。殺雷福海而毀其屍。襲破水尾房營,殲弁勇,劫掠軍械、火藥而南。七月,糾合呂家望社生番,焚毀臺東直隸州衙門,圍攻駐軍統領張兆連營。……時北洋大臣復派海軍統領丁汝昌以艦來援,艦礮可遠及番社,炸殺甚多,番懼乞降,許之。
這是與陳耀昌醫師「台灣史花系列三部曲」末部《苦楝花》三篇〈奇密花〉、〈苦楝花〕及〈大庄阿桃〉相關而被記載於史書的文字。全然以漢人官方的角度敘述其與阿美族、噶瑪蘭族、撒奇萊雅、大武壠族與馬卡道族之間戰爭的敘事。在這些漢人作者的描述,那些造成部落嚴重傷亡或導致部落瓦解、族人失散甚至族群滅絕、語言文化消失的戰爭,都原始都遭到扭曲,再以輕描淡寫的手筆賦予霸道、栽贓式的歷史注腳:開路,奇密社不服,殺林東涯以叛,番不支,乞降,許之/商人陳文禮至加禮宛墾田,為番所殺。營官令以金、穀慰死者家屬贖罪,番不聽,且殺傳令兵丁,與竹窩宛社謀叛。番悉服命/徵取田畝清丈單費嚴急,民、番胥怨;又拘辱其婦女,眾番忿;遂叛。炸殺甚多,番懼乞降,許之。
開路墾地,侵入別人的領域,或者是強徵苛刻的土地清丈費用,欺負部落婦女,這些事情,凡有血氣人性者遇上,任誰都要義憤填膺!林東涯、陳文禮、雷福海之流,在部落流傳的敘事都是仗勢欺人的惡棍,官府不僅不去懲戒、驅離,還放任其惡行,難怪要引起怨怒。至於如吳光亮等人的集體屠殺、凌遲毒計,以及以艦礮轟擊部落的行徑,有的史書刻意抹消,所幸當年自劫難逃脫者的敘述的口碑依然傳續,可以核對漢文紀錄的真偽。
陳耀昌醫師在《苦楝花》敘寫的故事,就是由歷史地點的踏查、相關人物的訪問逐漸形成的敘事架構。陳耀昌醫師以三種截然不同的寫作模式完成三篇不同歷史的表述。〈奇密花〉以一個現代女性研究者在偶然的夢境回返/進入大港口事件中吳光亮設計屠殺阿美族人的現場,在參與/陪伴/窺視的情境中,親睹/再現流傳在阿美族部落的自主敘事。〈苦楝花〉作者自言是模仿莎翁劇作的筆法,藉由噶瑪蘭族加禮宛社及撒奇萊雅族達固部灣社領袖(頭目)、青年領導者等的對話、情勢演進的敘說,以二十六幕呈現噶瑪蘭、撒奇萊雅兩族對抗清軍以至敗陣、逃離、失散百多年後,終於再凝聚的歷程。詩行排列的白話文辭,卻能有凝鍊、緊湊的表意效果。〈大庄阿桃〉以一個女性的角度觀看部落以及族人(尤其是男性)如何面對清代官軍的跋扈與地方官吏的醜惡行徑。再去看看局勢改變後,原本魚肉族人的清朝官兵們在遭部落戰士與日軍追殺時的狼狽。她的牽手阿勇也跟著部落的男人一起襲擊清軍兵營、官署,卻沒能保命回來。後來靠著項鍊,阿桃知道了阿勇最後的結局,也因為它而讓她願意收容離鄉背井的湘軍落地生根。〈大庄阿桃〉敘說自西部翻山越嶺來到東部縱谷尋找新居地的平埔族群如何想辦法生存的故事,在在展現女性的堅強與包容能量。
陳耀昌醫師靠著精準的觀察,以及他自言的好運氣,完整彙集了這些史事的部落觀點與在地說法。他確實也找到、遇到了跟這些史事具有關鍵意義的人物,得以更好佐證他故事/歷史的信實。所幸陳耀昌醫師的努力尋訪,讓這些故事/歷史再次被擦亮。奇美/奇密部落現在成為秀姑巒溪泛舟途中的休息點,南邊的靜埔與北邊港口部落,也是東海岸旅行者熟知的地方。達固部灣、馬立雲、加禮宛、新社等在撒奇萊雅與噶瑪蘭族陸續正名後逐漸為人所知悉。大庄/東里隱藏的故事在《苦楝花》中也被揭露了。陳耀昌醫師這本《苦楝花》應該可以讓行遊東部縱谷與東海岸的旅人得以增添更多歷史/故事探索的興味。有此榮幸得以先讀,謹以感謝、感動的心情作此序文。
二○一九年六月六日寫於壽豐
(本文作者為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院長)
‧摘文
第一部 奇密花
朱小君一天之中兩次得到旅遊的邀約,真是心花怒放。
上午,她在研究室,她的碩士論文指導老師在接了一個很長的電話後,告訴她:「一位廣東著名大學的歷史系教授來電,明年要在吳光亮的生日,在吳光亮故鄉舉辦一個吳光亮研討會。如果妳確定妳的研究題目是花蓮開發史,吳光亮是一個重要的人物,妳考慮一下要不要去。」接著又自言自語地說:「奇怪,吳光亮是一八三四年生的,明年二○二○,吳光亮一八六歲,不是二百周年也不是一五○周年……」
她知道吳光亮。唸台灣史的研究生無人不知吳光亮。一八七四年沈葆楨開山撫番,是台灣史的里程碑。開山,就是闢了三條山路,貫穿大山,到達以前難以到達的後山。這三位將領北路羅大春,中路吳光亮,南路張其光,從此名留台灣史。中路大約就是現在的「八通關古道」,由竹山(舊名林圮埔)到花蓮玉里(舊名璞石閣)。
八通關古道現在仍是許多登山者之上選路徑。但除了這個,有關吳光亮,她知道的就不多了。
好巧,當天晚上,她和男友吃飯,男友說,要給她一個可以永遠回憶的生日禮物──到秀姑巒溪去泛舟。男友興沖沖告訴她行程的安排:先到玉里過一夜,第二天早上搭火車到瑞穗。午飯後泛舟,大約一點半開始,自瑞穗大橋到秀姑巒溪出口長虹大橋。河段二十二公里,航程三至四小時。然後晚上在靜浦當地找一家民宿住,第三天早上去花蓮,再遊太魯閣。
她高興極了,拋了一個飛吻給男友表示滿意。男友是玉里人,兩人都在台中唸大學。她去年考上了歷史碩士班,男友則是另一所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住院醫師。交往近一年,她還沒到過男友家,也沒有去過玉里。她心中暗喜,她男友似有帶她見公婆的意思。
她完全未曾來過花東。她決定以花蓮的開發史為研究論文,只因為男友是花蓮玉里人。她本身是彰化人,對東部完全陌生。
男友聽到她明年要到「吳光亮研討會」,很高興地說:「那太巧了,我們玉里有一所大廟,和吳光亮兄弟好像頗有淵源呢!」
「我早知道啦。你們玉里是當年開山撫番中路,八通關古道的終點呢!有吳光亮的一些遺址是必然的。他弟弟叫吳光忠,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之戰時仍戍守東港,準備抗拒日軍。胡適的老爸胡鐵花在日記中也提到他。呵呵,我台灣史可不是唸假的!」男朋友作勢向她敬了一個禮。
老師既然要帶她去,不會沒有工作分配下來。於是她上網買了一本《吳光亮傳》,是台灣省文獻會一九九四年出版的,屬於「台灣先賢先烈專輯」,作者是一位文獻會約聘研究員。
這大概是台灣最詳盡的有關吳光亮的記述了。作者是竹山人,竹山正是「八通關古道起點」。小君不禁啞然失笑,真巧。這位作者因成長於八通關古道起點,而對吳光亮有興趣;她因男友成長於八通關終點而對吳光亮有興趣。這本《吳光亮傳》她匆匆讀過,她印象最深的是吳光亮光緒元年開通八通關古道,後來在光緒三年,有個「納納、阿棉事件」;光緒四年,又有個「加禮宛社事件」。
「加禮宛事件」她略有所聞,「阿棉社事件」則不太清楚。看了《吳光亮傳》的描述,又找了地圖(見夏獻綸之「台灣後山全圖」)來看,才有一些概念。光緒三年,吳光亮在璞石閣立了大營,然後要開闢水尾到大港口的道路。沿路阿棉、納納兩社不願,於是與吳光亮打了幾場仗,各有勝負。後來吳光亮一仗殺了一百四十位原住民,終於獲勝。而且光緒四年春三月七日,清廷以攻克阿棉、納納兩社「兇番」,賞台灣道夏獻綸封典、優敍,吳光亮與孫開華等黃馬掛,寬免副將林福喜等處分,並予陣亡都司羅魁優卹。這是她模模糊糊的了解。
吳光亮在那二個「討伐」事件後,寫了「化番俚言」,共三十二句,每句八個字,代表了那時漢人對番人為「蠻夷」、「缺乏教化」的看法。
她嘆了一口氣。這本《吳光亮傳》就是完全漢人中心觀點,對吳光亮全部正面描述,歌功頌德。也難怪,二十年前的書了。而台灣現在已經不一樣了,漢人已知道反省,原漢漸漸往平權邁進中。
後來她又買了一本吳光亮的奏章集,也是文獻會出版的「吳光祿使閩奏稿選錄」,都是一些文言文奏章,看了大失所望,沒有去唸。
※
小君和男友先搭高鐵自台中到左營,再轉台鐵,由左營到屏東。到了枋寮,小君不覺精神一振。這就進入一八七四年牡丹社事件時所謂「瑯嶠」,或一八七五年「開山撫番」以後的恆春縣地域了。火車經過加祿站、內獅站,小君更興奮,她讀過陳耀昌的《獅頭花》,知道這裡是當年大龜文部落酋邦內獅、外獅部落大戰清國淮軍之處。那是開山撫番後第一個原住民與清國官兵的戰爭。
火車進入大武山區,這是當年大龜文的心臟地區,風景絕美。小君和男友心情好High。車到大武,終於到了台灣的東海岸。火車沿著太平洋走,山勢、海景更是令人如醉如痴。過了知本之後,火車進入台東及花蓮的縱谷。荷蘭人、漢人進入東部「後山」,大抵就是這樣走的,先到台東,再到花蓮。一開始全稱為「台東州」,後來把卑南大溪流域稱為「台東」,把秀姑巒溪流域分出為「花蓮」。當年花蓮是台東州的一部分,但現在卻稱為「花東」,而非「東花」了,小君想。
車過台東,開始進入卑南大溪流域。她以前沒想到卑南大溪如此雄偉,縱谷又如此秀麗。過了卑南大溪流域,進入花蓮境內的秀姑巒溪流域後,第一個大站就是玉里。現在一般台灣人聽到玉里,大概只知道這裡有個大型的老兵醫院或養老中心,而完全不了解玉里在台灣開拓史的地位。連她男友都不知玉里舊名「璞石閣」,小君嘆息著。這也是她論文選擇「東部開發」為題目的原意,「其實我也是多知道一點點而已。」她想。
男友的父母,顯然對小君印象不錯,在晚飯時與她談了許多花蓮的美景與物產。他們很好奇小君為什麼唸歷史,問小君說,唸歷史除了當國中、高中老師以外,還可以有什麼職業?男友搶著回答說,當國中老師一年有三個月寒暑假,有什麼不好?!小君笑笑,沒有說些什麼,但其實心中有些不滿,她想,豈可如此小看唸歷史的。
第二天早上,小君和男友到了「協天宮」。這協天宮,以玉里小鎮的規模,可算是金碧輝煌的大廟。當年吳光亮在光緒元年開通了現在稱為「八通關古道」到璞石閣,第二年就立了這個廟,大概是在花東最有歷史意義的大廟了。那有名的「後山屏障」的匾額,掛得很高,加上歲月洗禮及焚香煙薰,綠底金字,小君看得吃力,也無法辨出題款的字。反而是她查了Google,知道這匾是光緒七年立的。「所以是那些事件以後才立的了」,小君想。
協天宮的廟埕立有一塊石碑,小君一字一字唸出碑文,邊唸邊笑出聲。
……西元一八七五年,運會所趨,交通首要,八通古道,迫於修建,自林圮埔至花蓮樸石閣(今玉里),通衢以來,吳氏昆仲,光亮光忠,率飛虎左營前駐,安屯之後,天意難料,瘟疫大行,手足惶錯,素仰帝君,仁義禮智,三界伏魔,爰築草屋,吳光亮將軍親題,後山保障匾額,以奉祀迄今。後山居民,族群龐雜,阿美布農,平埔客家,漢民雜處,嫌隙難免,爭端時起,幸賴神召,和諧共居。……
男友在旁邊補充著:「是啊,我們這裡的血統很複雜,高山原住民有布農、阿美,平地在閩、客之外,還有許多西部的平埔西拉雅或馬卡道,在十八、十九世紀因被漢人壓迫而越過中央山脈,遷徙到此。我本人是客家,我們祖先是清朝光緒年間過來的,雖然才短短五、六代,我懷疑我說不定也有平埔血統呢。」
對台灣史較熟稔的小君說:「你們這裡的平埔,是自台南頭社或玉井一帶遷來的。他們認為自己是大武壠或大滿,與西拉雅有些不同。另外有些是由屏東林邊放索、萬丹一帶,經由浸水營古道遷來,他們則認為自己是馬卡道,不是西拉雅,也不是大武壠。你們家混的,是大武壠還是馬卡道?」
男友苦笑道:「妳問我,我問誰啊?」又問:「妳剛剛為什麼一直笑,在笑什麼?」
「好啦,」小君笑道:「其實我是笑這碑文的文字,道盡漢人的偽善與假仁假義。我們唸歷史的,都知道吳光亮在後山,殺了不少原住民,但他卻頒布了〈化番俚言〉,好像他只強調感化,從不殺戮似的。過去漢人統治者一貫如此,滿口仁義道德,作為凶狠毒辣。這也許就是原住民一直不喜歡漢人,不信任漢人的原因吧。」
小君又說:「例如剛剛大殿那個『後山保障』,大家認為吳光忠所題的匾,又是另外一個例子。『後山保障』,保障了誰啊?後山本來是原住民的,難道是吳光亮保障了原住民嗎?恰恰相反,是保障了入侵後山的漢人啊!。」男友在一旁苦笑著。
小君看到表情尷尬的男友:「唉,現在是多元共榮啦,也沒要你們漢人搬出後山,只是要你們不要繼續這一付道貌岸然,滿口道德的漢人沙文主義觀點就是。」又說:「高中課本決定不採用連橫的《台灣通史序》,就是因為原住民詩人莫那能的一句話:『你們的篳路藍縷,我們的顛沛流離!』」
男友打哈哈說:「只道你們這些唸歷史的最冬烘,誰知反而思想最前衛,最進步了。佩服佩服。」
小君說:「唸歷史是為了反省,以史為鏡,說的就是這個。你們學醫的,醫人醫獸;我們學歷史的,醫國家醫社會,作用大著呢,豈是為了三個月寒暑假。」
男友說:「哎呀,失敬失敬。我必須多了解一些台灣史了。」
小君笑說:「那還用說!」但又感慨。她說:「其實,在台灣史方面,我們過去承緒了太多漢人史觀,都是一面之詞,因此要好好重新評估。許多歷史事件,原住民的觀點沒有能留下來,因而真相不太清楚。例如這位吳光亮,在〈化番俚言〉卷首,又加了一篇光緒五年(一八七九)『諭後山各路番眾』的曉諭,也說得冠冕堂皇。先舉前幾年阿棉、納納、加禮宛等社,經吳光亮『親統大軍,嚴加痛剿,以張天威』,然後經過設立番學,教番童識字讀書,最後以這三十二條『淺近野俚』的《化番俚言》,而使『蠻夷僻陋之俗,轉成禮義廉讓之風』。」
小君有著感概。加禮宛事件她略知一二,但阿棉、納納的地名今已不存,因此不知詳情。但總之,這就是台灣原住民的「被漢化過程」,當然包括日常風俗的改漢姓、穿漢服…等,把「漢化」當「教化」。小君感慨著,這就是過去不尊重少數族群的漢人沙文主義及擴張主義,自以為是的偏見。
一直要到這幾年,台灣社會才慢慢了解原住民文化有其融自然天地於一體的優點。在過去漢人讚美「人定勝天」、「愚公移山」、「戰勝大自然」的時候,漢人看不到原住民優點,認為原住民懶散、笨拙,只會唱歌跳舞。要等近幾年屢屢出現大自然的反撲之後,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住民文化比我們看得更遠……。其實日本人早看出了這一點。森丑之助說,站到山上,青翠的地方就是番人的,光禿禿的地方就是漢人的。這正是現代才有的「水土保持」的生態思維。而當年,則視為原民之疏懶。在一九二五年之前,森丑之助就看出了原住民文化的優越,但他也無法勸服那個年代的日本總督府,所以他只好在基隆港跳海…。
在火車到瑞穗的途中,小君一路上讚嘆著窗外花東縱谷的秀麗景色。她的男友,則臉色有點臭,帶女友來旅行,女友則沒有柔情蜜意,而卻鍾情於歷史和原住民,還一路上談歪理,倒有些像是在譴責他。
最新生活新聞
-
充滿人情味的文化交流盛宴 華大溫馨聯誼陪伴國際生融入校園生活
(7 小時前) -
明新科大59週年校慶 關鍵字「底氣」象徵59年來累積的實力與自信
(8 小時前) -
彰化榮服處替代役男敬老傳愛 關懷榮民長輩
(8 小時前) -
臺東榮服處與北榮東院榮民文物展 見證退除役官兵篳路藍縷
(8 小時前) -
重陽關懷長者 竹郵局長吳進益:善盡社會責任分享公益慈善喜悅!
(8 小時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