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教弩臺/方克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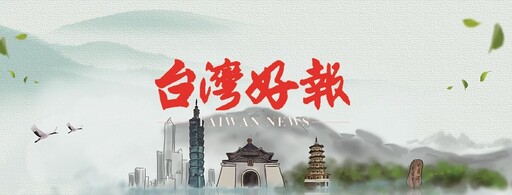
方克逸
江淮風景名勝曹操教弩臺(明教寺),位於安徽合肥市區淮河路步行街,百姓俗稱“曹操點將臺”,現名“古教弩臺”。1981年定為安徽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臺上建有佛教叢林明教寺,被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開放寺廟,是合肥最古老的佛教寺院。二者兼之,乃合肥重要地標之一。
曹操教弩臺(明教寺),現面街高約五米,面積約4260平方米,略呈正方形。台基陡峭,邊緣勒以磚石。清嘉慶《廬州府志》載明教寺辭條:“明教寺《輿地紀勝》:在城歲豐橋北,即魏武教弩臺。唐大曆中,因得鐵佛一丈八尺,一丈八尺,奏為立院。明張唯恕詩:魏國爭分鼎,臺經幾度過。回風悲鼓吹,落日見山河。西蜀初相制,東吳未肯和。即今歸聖統,共聽太平歌。徐師騫《春日偕同人登明教臺詩》:魏武今安在?淮南尚有臺。昔時神弩盡,此日雨花來。懷古群雄失,談經寶刹開。登臨忘色相,生意燦寒梅。”《嘉慶·合肥縣誌》載:三國鼎立時期,合肥屬魏,“魏之重鎮在合肥”。魏主曹操四次蒞臨合肥,築此高臺教練強弩兵將,以禦東吳水軍,故名“教弩臺”。
步入曹操點將臺舊址,教弩台東首有一座六角亭,亭額:“古屋上井”,亭中有囗水井,因井口高於教弩台下民房屋脊而得名“屋上井”,志書則曰“高井”。昔日遊人躬身下望,能見井水,其水位比當地水位高出許多,令人歎為觀止而成費解之迷。相傳屋上井水味甘美,四季不竭。該井是當年魏軍為汲水所鑿,至西晉時得到整修。井欄石圈呈斑駁陸離滄桑感,依稀可見鐫刻“晉泰始四年殿中司馬夏侯勝造”的隸體字跡,系西元268年的古跡,井欄圈口遺下汲水繩磨成的23條索溝,堪為千年曆史之見證。如今屋上井口已加蓋井罩,以予保護。
距離屋上井附近,有三國遺跡“聽松閣”,乃當年曹操麾下強弩手稍息納涼的地方。史傳曹操坐陣教弩臺排兵佈陣,檢閱五百名弓弩手在此操練,勝者贈與紅袍以示獎勵。逢百步穿楊者,鑼鼓聲驟起,贏得曹操暢快大笑。由於合肥夏天炎熱,為使士兵盛夏不受日曬,曹操便令廣植松柏。松樹長成後,清風襲來,松濤陣陣。後人為了緬懷前賢,在此建閣,聽松閣隨之得名。閣上懸有楹聯:“教弩聳高臺不為炎劉消劫難;聽松來遠客誰從古佛識真如。”
曹操(西元155~220年,字孟德,小字阿瞞 ,今安徽亳州市人, 東漢末年的權臣,曹魏政權的奠基者)軍事、文學並駕雙雄,當年屢蒞教弩臺,傳聞留有“登臨收楚豫,吞吐盡江淮”詩句。三國以後,唐人吳資曾作五言詩曰:“曹公教弩臺,今為比丘寺,東門小河橋,曾飛吳主騎。”闡明了教弩臺和明教寺的相互關係。宋人朱服《過廬州》詩雲:“柳塘春水藏舟浦,蘭若秋風教弩臺。”亦申此意。歷代文人墨客登詠教弩臺,使得三國故臺縈繞詩情畫意。隨著光陰荏苒,時移景遷,昔日松蔭密蔽的教弩臺,一度成為荒臺,明人熊敬曾觸景感歎:“ 落落松蔭掃不開,亂蓬遺棘翳荒臺。奸雄已死三分後,教弩何人更此來?”
教弩臺上明教寺始建於南朝梁武帝年間(502~549),為明朝院式建築,屬禪宗五家之一臨濟宗,迄今已有1700餘年歷史,演繹了南朝至明朝及民國時期和解放後中國江淮佛教文化的發展變化。該寺原名“鐵佛寺”,建成後不久荒廢。唐大歷年間(766~779),有人於教弩臺廢墟掘得丈八鐵佛一尊,廬州刺史裴絹奏聞朝廷,代宗皇帝李豫聞奏甚喜,敕令重建寺廟,賜名“明教院”,明代改稱“明教寺”,沿用至今。
該寺在清代鹹豐年間毀於兵火,現存雄偉莊嚴的大雄寶殿,系鄉賢袁宏謨籌款所建。據原有寺牆石碑記載,袁宏謨曾是太平軍將領,太平天國失敗後,削髮為僧,號通元上人,先是在肥西縣紫蓬山西廬寺出家,後參禪於明教寺(為西廬寺下院),經多年苦行募化,終於在光緒十一年(1885年)重建了明教寺,被尊為“中興始祖”。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人民政府曾多次撥款維修教弩臺(明教寺)。現明教寺佛像共有30餘尊(其中銅佛5尊)。有山門、大雄寶殿、天王殿、地藏殿、教弩梵鐘亭和客堂、寮房等建築,計800餘平方米。現殿中三世佛塑像為明代作品。殿內的大鼓和銅鐘系清代製作,大鐘高2. 02米,直徑1.52米,四周滿鑄佛名和鐘偈花紋,鐘面鑄有“明教寺”字樣。寺內晨鐘暮鼓,梵音繚繞,洋溢清幽神奇的宗教色彩。
教弩臺原在合肥城之外,宋朝時候,合肥城擴建,教弩臺被圈入城內,成了合肥城內的著名景點。近二千年來,合肥城雖經歷了無數次的風風雨雨,但教弩臺始終巍然屹立,目睹了合肥城的滄海桑田。明教寺由佛殿、藏經閣、西廂院三部分組成。殿分正殿和後殿,有佛像三十多尊。明教寺山門建在一梯形臺階上,為單簷歇山式卷棚頂。大雄寶殿為重簷歇山頂,高數丈,飛簷翹角,朱簷簡瓦,風鈴叮鐺。殿脊高聳一巨大錫葫蘆,銀光閃耀,直射雲天,彰顯了我國佛教寺宇威嚴莊重的建築特色。大雄寶殿旁有屋上井亭、教弩亭等景點,整座寺院軸線基本對稱。
明教寺現任住持為百歲高僧方丈妙安大和尚。安徽省並合肥市佛教協會也設在此處。
教弩臺(明教寺)與淝水、津水和三國古戰場逍津咫尺為鄰。《廬陽名勝便覽》稱立於此臺,可見“墟煙如帶,漁火搖紅”,俯瞰合肥全城。其以“教弩松蔭”風光,享譽廬陽八景之一。康熙貢生、廬州府學正朱弦著《八景說》,其中《教弩松蔭》全文曰:
九獅橋北,土阜巍然,乃曹公教弩處也。四圍陡削,磚以植之,躡磴而升,計三十有三級,空臺濯濯,安有松陰?當時曷言乎松陰也?想孟德教弩時,揮汗如雨,應植大夫於其上,以陰壯士。歲月既久,柯化龍麟,針成鶴翼,後人因指為松蔭雲。因而,思老瞞作銅雀臺於漳水,上聳百尺,下蘸淸流,圖置二喬於中,諸臣賦詩飲酒, 以極一時之盛事。至於今,美人何在?銅雀臺化為烏有,僅餘漁歌、樵采、荊叢,狐穴而已。反不如此臺,以不革不美存。存則存矣,松陰安在邪?然中央佛殿軒軒霞舉,一周匝以僧舍,每黃昏清旦,淵淵木魚,一派梵唄,有類海潮之音,又何減十裏松風邪?即謂松陰至今存可也。
朱弦美文,字字珠璣,以教弩臺蓋壓銅雀臺之內涵大義,流光溢彩,警醒世人。
辛醜荷月,筆者複登教弩臺,流連明教寺,倚臺極目科技高地、大湖名城之合肥,但見車水馬龍康莊路,櫛次鱗比樓宇雄,心曠神怡,浮想聯翩,感慨而即興撰成楹聯系之,晉見求教百歲高僧妙安大和尚,幸獲首肯。聯雲:
登教弩三國故臺,松蔭淨土,化干戈為玉帛;
拜明教承平造化,普惠眾生,祈海晏與河清。
最新生活新聞
-
-
小酌食趣2/紅磚老宅變身新型態社交沙龍 LAY LOW不只餐酒還有DJ表演
(2 小時前) -
小酌食趣1/來台中最新深夜食堂「好夜」報到 嘗台味小吃尬本土、南洋風調酒
(2 小時前) -
7-9月護蟹交通管制 台江國家公園「蟹謝」配合
(2 小時前) -
彰化縣 一週天氣預報(06/29 05:00發布)
(2 小時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