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霞客遊記的龍泉寺及勐氏歷史脈絡/許文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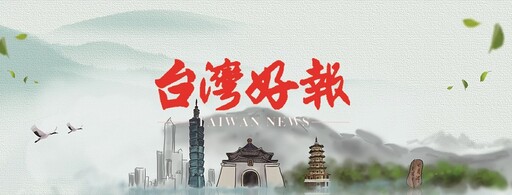
許文舟
徐霞客(1587年1月5日-1641年3月8日),名弘祖,字振之,號霞客,南直隸江陰縣(今江蘇省江陰市)人,明代地理學家、旅行家和文學家,他經30年考察撰成了60萬字地理名著《徐霞客遊記》,被稱為“千古奇人”。1639年八月初五,徐霞客從保山抵達鳳慶,並在此考察11天,留下了萬字日記,其中囊括了山水地理、民俗人文、歷史文化等諸多內容。
早在徐霞客從永平到永昌的途中,瞭解霽虹橋的情況時,徐霞客便已對勐(古稱猛)氏有過瞭解。“萬曆丙午(1606年),順寧土酋勐廷瑞叛,阻兵燒毀。崇禎戊辰(1628年),雲龍叛賊王磐又燒毀。四十年間,二次被毀,今己巳(1629年)複建,委千戶一員守衛。”該文記載了萬曆丙午年(1606年)和崇禎戊辰年(1628年)兩次被毀又重建的情況。這一事件的記述可能源於史述,如明天啟《滇志》就寫道:“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為順寧勐酋所焚,兵備副使邵以仁重建,二十八年(1600年)複毀,兵備副使杜華先、分巡按察使張堯臣捐俸修,知府華存禮請於兩岸設弓兵守之。”該文記載了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和二十八年(1600年)兩次所毀又重修的情況。雍正《順寧府志》收錄了田世容的《焚橋辨》,論證勐廷瑞受灣甸土知州嫁禍而冤死,給出了勐廷瑞靈驗和彝人崇拜猛廷瑞的一種解釋。關於勐氏焚橋,最早見於《明實錄》,但未指出所燒是何橋。天啟年間,猛氏焚橋說在天啟《滇志》中再被提及,勐廷瑞“弄兵官道,燒古鐵橋”,且收錄的《霽虹橋記》《重修霽虹橋記》明確指所焚之橋是永昌府境內瀾滄江上的霽虹橋,且是勐廷瑞所焚。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府志餘抄》首次提出焚毀霽虹橋乃灣甸土知州嫁禍。至此,焚橋者由順寧土官勐廷瑞轉為了灣甸土知州。也可能源自田野調查,從當地人口中得知,我們不能確證,但可以知道的是,徐霞客對土酋勐廷瑞是有過瞭解的,並且由於歷史的原因,徐霞客對土酋勐廷瑞的好壞沒做過評價,只是依據史料進行記錄。
1639年八月初七,徐霞客離開勐佑村,前往縣城。由於千百年的雨水沖刷,從勐佑起到縣城的路差不多都在溝槽裏行。直到那翻過中和村抵達望城關,走得異常辛苦。從望城關到府城是十裏,均是逶迤下坡,路倒也漸漸寬起來。坡腳到府城新城的北門,足有二裏。這時已是下午,穿過一條街走出南門,進入龍泉寺。龍泉寺所在的位置叫舊城,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城池。此時,龍泉寺開堂講經剛完,僧俗熙熙攘攘,正准就餐。徐霞客此刻也是饑腸轆轆,顧不得那麼多了,撂下擔子,飽餐一頓,晚上就在寺內住宿。第二天離開龍泉寺到雲縣,再到初十一日,回到龍泉寺。徐霞客一生志在四方,足跡遍及今21個省、市、自治區,“達人所之未達,探人所之未知”,所到之處,探幽尋秘,並記有遊記,記錄觀察到的各種現象、人文、地理、動植物等狀況。他不僅是偉大的旅行家,更是一位佛家居士。他的《遊記》有濃厚的寺廟情結。徐霞客以優美、生動的筆觸將他所欣賞的、敬仰的寺廟記錄下來,對這些寺廟的選址、環境及內飾等都做了詳細的描寫,並在其中形成了自己關於寺廟的審美觀。徐霞客的審美觀在《遊記》中雖然是散見在他對各個寺廟的描述中,但卻是徐霞客從旅遊的角度出發,將寺廟不只作為棲身拜佛之所,更作為旅遊對象和審美對象加以欣賞、品評後的美學思想的凸顯。徐霞客關於寺廟的審美觀直到今天依然具有積極意義,對於我們維護古寺建築,更好地欣賞名寺古廟有極大的幫助,甚至對於我們今天進行旅遊景區的開發也有相當高的借鑒價值。
《順寧府五部志》載:“龍泉寺外有水一泓,不盈不竭,自龍王法座下洑流而出,漾為漣漪。亭立雙橋,池開半畝。春則花明柳暗,遊人坐以清心,秋當月湧星沉,知者其無垢。”雍正《順寧府志》記載:龍泉寺“在城南裏許舊城。明天啟四年(1624)建,舊為土府勐氏園亭。康熙三十三年(1694),知府徐欐重修。”龍泉寺,在城南一裏舊城。鹹豐丁巳年(1857),兵燹毀。光緒五年(1879),僧真檀重建大殿、文樓。十一年(1885),紳士重修大門。十九年(1893),重修水閣。二十七年(1901),重修池塘、圍牆、圈橋,租穀二百二十餘孔。”吾邑舊有順寧十景,不知名之者誰?名之於何時?而《雍正順寧府志》載之具矣。三韓李文淵有十景吟詩,其中《龍湫泛月》在十景之首:清泉脈自海門通,知有潛龍臥壑中。固織冰綃奩玉鏡,平拖素練出晶宮。風鳴翠柳偷青眼,雨濯金鱗啖落紅。尺蠖此時澄萬類,夜深聽法不曾聾。
從徐霞客在鳳慶幾天的情況看,吃住差不多都與寺廟有關。這不得不說徐霞客與寺廟的緣分了。從徐霞客遊記裏不難看出,徐霞客在旅途中廣交僧侶,誠心禮佛,談禪論道。佛教對徐霞客的支持也是最多的,物質上的精神層面的都有。到第三階段的征途“西南遠征”時,徐霞客已經50歲了,後期的他幾乎可以說是窮遊,家裏的資產經他一折騰財力已難以為繼。8月11日下午,徐霞客出東山寺,過亭橋,入順寧東門。這次重入龍泉寺,遇上了曾在永平慧光寺相識的四川一葦法師。一葦法師為徐霞客泡茶煎餅,兩人相談甚歡。龍泉寺已不復存在了,但通過徐霞客的記錄,似乎又聽到龍泉水嘩嘩流過。寺裏的住持除了好茶待客,還“為餘瀹茗炙餅,出雞葼、松子相餉”。380多年前的鳳慶人,多麼熱情!
就是吃住過的龍泉寺,竟然與鳳慶歷史上影響重大的勐氏歷史有關。己卯年(崇禎十二年,西元1639年)八月十四,徐霞客早晨起床吃飯,準備跟著馬上到巍山時,因馬幫等候收取鹽款,所以徐霞客從早上一直等到中午。徐霞客沒有親著,而是通過實地走訪與考察,對鳳慶的歷史有了更深入的瞭解,尤其是鳳慶歷史上的勐氏歷史。在他的遊記裏寫道:
“順寧者,舊名慶甸,本蒲蠻之地。其直北為永平,西北為永昌,東北為蒙化,西南為鎮康,東南為大侯。此其四履之外接者。土官猛姓,即孟獲之後。萬曆四十年,土官猛廷瑞專恣,潛蓄異謀,開府高級武官陳用賓討而誅之。大侯州土官俸貞與之濟逆,遂並雉狝伏法治罪之,改為雲州,各設流官,而以雲州為順寧屬。今迤西流官所蒞之境,以騰越為極西,雲州為極南焉。
龍泉寺基,即猛廷瑞所居之園也,從西山垂隴東下。寺前有塘一方,頗深而澈,建水月閣於其中。其後面塘為前殿。前殿之右庭中皆為透水之穴,雖小而所出不一。又西三丈,有井一圓,頗小而淺,水從中溢,東注塘中淙淙有聲,則龍泉之源矣。前殿后為大殿,餘之所憩者,其東廡也,皆開郡後所建。舊城即龍泉寺一帶,有居廬而無雉堞。新城在其北,中隔一東下之澗。其脈亦從西山垂隴東下,謂之鳳山。府署倚之而東向。餘入其堂,欲觀所圖府境四止,無有也。”
順寧,舊時叫慶甸,本是蒲蠻的地方。土官姓猛,是孟獲的後代。萬曆四十年(西元1612年),土官勐廷瑞專權放肆,秘密蓄謀反叛,開府陳用賓討伐誅殺了他。大侯州土官僚貞與他一同叛逆,就被一起殲滅了,改成雲州,各自設了流官,把雲州劃成順寧的屬地。龍泉寺的基址,是勐廷瑞居住的花園,土隴從西山向東下垂。寺前有一片池塘,相當深而且池水清澈,池中建了水月閣。它後面面對池塘建成前殿。前殿的右側,庭院中全是出水的洞穴,雖然小一點但出水的地方不止一處。往西有一眼井,很小,又淺,水從井中溢出,向東注入池塘,塗塗發聲,那是龍泉的源頭。前殿后是大殿。徐霞客曾經歇息的地方,是大殿的東廂房,是設府後建的。
舊城在龍泉寺一帶,有居民房屋卻無城牆。新城在它北邊,中間隔著一條往東下流的山澗。這裏的山脈也是土隴從西山向東下垂,稱鳳山。府衙背靠鳳山面向東方。徐霞客進入府衙的大堂,想觀看地圖上府境周邊情況,卻沒有地圖。順寧府城所依託的山峽,狹窄不開闊,只不過是兩座山中間的一個山塢罷了。本處山塢不如右甸那樣又圓又平展,四旁山塢也不如孟枯村那樣交錯紛繁。這個山塢西北起自甸頭村,東南到函宗有一百里,東西寬處不到四裏。順寧府的地域,北邊寬而南邊窄。由府城往南,是灣甸、大侯兩個州,在東西兩面夾住它,尖得好像犁頭。
由龍泉寺牽出勐氏歷史,篇幅雖然不長,卻基本可以理清勐氏在鳳慶的歷史脈絡。翻閱《順寧府五部志》,勐廷瑞史事的記錄者,有官方史官、任職雲南官員、客居雲南外省士人、雲南本土士人等,其身份多元,其看法各異,主要有兩種論述:第一種是猛廷瑞“焚劫煽亂”,李先著“納賄縱賊”,明朝平定順寧,改設流官。第二種是強調猛廷瑞蒙冤、李先著被誣。後來的清朝對猛廷瑞敘事的再構建,基本還原了猛廷瑞事件的真實性。當然,清朝在關於猛廷瑞的論述中加入了新的故事情節,在康雍乾時期,逐步形成了統一的猛廷瑞敘事基調。這一時期,正史、私人撰述和地方誌關於此事的論述僅在細節上有一些差別,地方誌補充了當地的軼事和傳說,出現了將明代官方文獻糅合進地方社會傳說的歷史敘事轉向,使勐廷瑞敘事成為一種符合官方標準的地方性話語表述。
勐廷瑞從小豪爽任性,又在前土知府勐寅順寧城創建的萬卷樓中飽讀苦學,頗有才幹。成年後,先娶灣甸州土官景宗正之女為妻,結婚幾年後,夫妻感情破裂,妻子回了娘家。後來,勐廷瑞又聚大候(雲縣)奉學女為妻,當時雲縣土官奉赦與弟奉學不和,廷瑞袒護奉學,那畢竟是自己的岳父大人,結果導致奉家兩兄弟經常爭端不止,刀兵相見,社會不得安寧。到了明萬曆二十五(西元1597)年,雲南巡撫陳用賓得知順寧、雲州兩地爭鬥的事,隨即委派瀾滄江兵備道參將李先著、金騰副使邵以仁到鳳慶一同查辦勐、奉兩家之憤。李先著先到鳳慶,與勐廷瑞面談,將其與大侯結仇互鬥之事曉以利害。勐廷瑞聽先著一番開導後,讓兒子手持黃金千兩和印信,一同與其子跪拜於李先著面前,聽候處理。當初李先著不願接受千金和印信,但經廷瑞父子苦苦相求,才接納獻金,充作軍用,並准予改過自新。邵以仁卻暗中向勐廷瑞索賄不得逞,便以“通彝納賄”之罪名誣陷李先著,並上訴巡撫陳用賓。陳用賓不辨真偽,就轉報朝廷,將李先著逮捕,同時,奉旨征剿勐廷瑞。勐廷瑞為表其忠心,斬殺奉學,獻子獻印,最終不得解脫,一場被征剿的厄運就這樣降臨到自己的頭上。1597年10月,邵以仁進剿勐氏石城,搜取勐氏18代積蓄無數。用計誘捕勐廷瑞父子,押解朝廷報捷,勐氏父子途中不幸斃命,勐氏所轄13寨不服,起兵反抗,被官兵剿除。勐氏家族於是偷偷改漢、彝等民族,有的隱姓埋名改姓為字、楊、紀、蔣、張等,得以在鳳慶倖存下來,有的向南遷逃,藉以躲避,而大部分慘遭殺害。
在鳳慶的許多地方,都有勐氏的遺址。其中較為著名的是勐氏石城為勐氏部落城堡遺址,位於新華鄉牛塵山中部,當地人稱“勐家地址”。距今400多年的勐氏部落的城堡,以石築成,故名石城。遺址坐南向北,東面懸崖峭壁,西北為松林陡坡,僅南向有一公里多長的山梁切成3段,距石城300米左右有一口井,可供守城人飲用。勐氏城東、北、西三面以騰索塔木排,上壘石頭如遇敵來犯,就砍斷騰索,滾木檑石傾瀉而下,守兵僅扼南面,易守難攻,是當時部落所建的重點城壘之一。
慶甸遺址坐落在雲南省鳳慶縣鳳山鎮麥地村明王室(寺)後的老君山峰獻山頂,距縣城(鳳慶縣)約5公里,為元朝天順元年(1328)所置勐氏衙門。《一統志》記載:“在城南八裏,本蒲蠻所居。元泰定中,始內附。天曆中,始置府及縣。明初省舊志,廢址猶存。”試用知縣太和歲貢生周宗洛寫過《過慶甸廢縣》一詩。“白草萋迷匝野棠,城南秋色莽蒼蒼。山空禾黍餘殘堞,水繞瀾滄識歸疆。鐵券何辜嗟覆滅,蠻花無語吊興亡。焚橋冤獄悲今古,野老千秋話夕陽。”此詩側面反映了那段霽虹橋因“順寧土酋勐廷瑞叛,阻兵燒毀”的事,其實那是冤枉勐廷瑞了。明洪武十五年裁縣後,即為勐氏部族首領的衙門,為勐氏十三寨之一。明萬曆二十五年(1597)滅了勐氏,二十六年“改土歸流”(改世襲土官制為朝廷派流官制)後即廢。現遺址猶存,當人地稱為“勐家衙門”。遺址坐東向西,為前後相連的三個山包,各相距約百餘米,據當地民間傳說,三個山包各為前殿、中展和後殿,中殿和後殿為土官居住和辦理政務的大堂,前殿主要眷屬飲食起居。選此為衙置,地勢險要,其安全真可謂萬無一失,衙門北面山腳有井一口,井水清澈如鏡,四時不竭。衙署前約三四百米處有一小山,山頭平坦,是雜役人員和衛軍居住的馬圈,後人稱為“勐家馬圈”。滅了勐氏後,二十六年第一任朝廷命官到任,此後,順寧世居勐氏或被斬殺或望風而逃,或改從其他大姓,“勐家衙門”即毀。新中國成立後曾先後出土1.25千克銀元寶4個及明代文物數件。其外,尚有勐土府舊址,“順寧府志”載,“在舊城,今之魁閣,即勐氏望樓也”。
境內瓊英洞洞內有土知府勐寅書寫“瓊英洞天”四字。“順寧府志”記載:“土酋勐氏曾率人秉炬行百里,豁然開朗,有大溪亙絕,隔岸桃花濃豔,恨無舟,不能渡,廢然而還”的傳說。瓊英仙洞位於郭大寨彝族白族鄉大力色村的越勝橋松澗下,離縣城80公里,原稱“阿度吾裏”。瓊英洞在數十丈懸崖之下,有洞穹窿高敞、流鐘乳作瓔珞,如鈿釵、如石筍、如芝田、如麥隴,不可名狀。山泉倒流入洞。 瓊英洞中有石桌、石橙、石象、石馬、石田、石山、石鐘、石鼓、擊石鼓石鐘,鳴聲甚洪。
象莊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元、明兩朝,是古代勐廷瑞土酋養象的地方。象莊位於雲南臨滄鳳慶,是未改設流官時土人酋長猛廷瑞養象的處所。這裏曾是古代貢象之路的必經之地,有“白象之瑞”的祥瑞之事記載。徐霞客在遊記中記載了關於勐廷瑞的事蹟。西元1639年八月初八,徐霞客抵達象莊,並在其遊記中記載道:“此處即為象莊,乃昔日猛廷瑞土酋蓄養大象之地,後因改土歸流而衰落。元、明兩朝,順寧府境內曾有一條專為貢象而設的道路,並曾記載有‘白象之瑞’的祥瑞之事”勐廷瑞是元、明朝代順寧府境內的一個土酋,他負責蓄養大象並向朝廷進貢。徐霞客在遊記中提到,這裏是古代在改土歸流前,猛氏土酋給朝廷進貢大象的必經之地。元、明朝代,有一條貢象之路橫貫順寧府境,曾有“白象之瑞”的記載。象莊的地理位置和歷史背景使其在古代具有重要的戰略和經濟意義。元、明兩朝,順寧府境內有一條專為貢象而設的道路,象莊作為土酋養象的地方,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儘管現代象莊已不再有養象的記錄,但其歷史和文化價值仍然被當地人銘記。
離城三公里的象塘,傳說是勐氏供大象飲水的地方,至今也只有一個名字成為行政辦事處的名稱。《順寧府志》記載:“象塘,在府城西南,明土府飲象處。今改為象塘寺。”同樣是府志所載:“如果庵,在府城西南三裏,俗名象塘寺,明時為勐氏飲象所。順治十八年(1661),蜀僧廠蓋募建,十年乃成。至康熙四十九年(1710),知府李文淵創修作十暇園,以瓷遊詠,清幽爽豁,草木生香,為禪林小勝。”知州王祚興寫過“象塘山如是庵記”名文,寫到“半世浮蹤,歷盡顛危之境,一朝厭俗,頓生超脫之心”的僧人廣蓋。寫過“金鐘扣缽,則萬籟聲傳;玉盎燃燈,則群迷路覺”的廟宇。行文最後落腳勐氏,縱然已物是人非,因為象塘一名,自然免不了一番思念。
龍泉寺及“龍湫泛月”。龍泉寺在縣城以南500米舊城龍泉街西,虎山社區東面,現存龍泉古井一眼,在其後面便是歷史上順寧土知府勐氏的後花園。無朝泰定二年(1325),內附後,被設法敕封為順寧土知府,明朝建立後,勐氏仍然當任土知府,前後治理順燈270年,其第十八代孫勐廷瑞被冤死後,遂將勐氏的土司後花園改建為龍泉寺,從西上重隴東下,寺前有塘一方,頗深而清滿澈,建水月閣於其中,前面後殿。清朝康熙33年(1694),順寧知府重修,內有十五殿,有龍泉伏流而出,水清質好,不盈不固,有“龍湫泛月”之景,清鹹豐丁巳年(1857)被兵火焚毀,清光緒五年(1879),僧人真檀重建大殿,及兩廂文樓。光緒十一年(1885),重修水閣,府官田亮勳題寫“鐘靈毓秀”四安為水閣橫匾,光緒二十七年(1885)重修池堂,圍牆、圈橋。當地士紳袁慎夫寫過“觀魚記”,用大理石刻碑留存。民國以來,將龍泉寺改建為小學,1943-1945年改作中國遠征軍赴緬作戰的轉運站。1965年在龍泉寺址改建為鳳慶縣造紙廠,利用當地原料生產土草紙,1995年因造紙污染環境,縣紙廠搬遷到現在的“綠茗花園”。原廠址為作為國有土地賣給居民建房,現在除了擠在居民區的一眼古井,基本上就都是一片現代建築了。
勐氏在順寧府城,仿照天上的北斗七星狀,修建了“七星井”。就是勐氏解決府城居民用心而精心修建的。歲月倏忽,600多年的歷史過去,許多古井在附近居民的維護下,仍然綠水蕩漾。除了舊城石水缸無水源外,其餘6個古井仍然水源旺盛,不竭不盈。雖然,城裏的居民都改飲自來水了,但縫年過節都能看到到古井取“新水”的居民。隨著時間的推移,很少有人再關注這些古井了,但古井的名字卻成了這些街巷的名稱,比如“雙眼井”,原來就是位於鳳城大東門外中段往東向斜坡60米的山嘴子,現在卻是一個文明社區下麵的一個小姐。雙眼井還在,只是因為居民驟增,水質已被污染,不再飲用,而雙眼井之名,因為其歷史原因,已成了縣城的一個古跡。
勐家大地基,位於鳳城至魯史公路瀾滄江邊地段的大山梁子腳,相傳勐家大地基是勐氏的搖籃,勐氏族人有21代在這裏生息。這裏地勢險要,高居大山梁子尾段上,左右兩邊均為懸崖峭壁,僅上下兩條退道可以入寨。從軍事角度上看,非常易守難攻,勐家大地基就位於主脈中段。而在離勐家大地基十多公里的勐家大廟,位於鳳慶縣大寺村村公所附近,原系勐氏用於祭祀的主場所。據鳳慶縣文史資料記載,勐家大廟初建於明朝初年,領地面積三畝多,主建築包括大殿及左右兩偏殿。明萬曆二十六年(1598),明軍鎮壓了反明武裝後放火燒毀勐家大廟,直至清朝康熙三十一年(1692),為緬懷勐氏先人,那些當年被迫改名換姓的族人自發捐錢捐糧,在原址上重建恢復了勐家大廟,年節之日香火不斷。1935年除夕之日 ,廟內香火引發火災大廟再次被燒毀。
勐家遺址,位於離縣城13公里的靈應山一個叫虎山頭的地方。《順寧府五部志》載:“靈應山有村曰虎山頭,山麓結坪,勐家遺址在焉。相傳為第五圈圈官衙署,其面廳為曇華寺,移作過樓,雕樑畫棟,古老斑駁,尚未朽,基石為村人拆用。魚池一方,僅出水處為村民之井,餘皆為耕地。現存兩柱墩專柱平面,直徑二尺餘,刊花石板數塊,亦尚存民家。冬棕轎杆一棵,保存於厚豐村後靈山勐府祠中,留為勐氏紀念。傳曇華寺大銅香爐一座,低印大明宣德,亦勐家遺物也。”
徐霞客在鳳慶的時間裏,兩次走過的“歸化橋”,同樣是有勐氏有直接關係的遺存。《順寧府五部志》載:郡東南十裏許,當雲緬各縣入順之孔道,有橋曰“歸化”。夫橋何以歸化名?未由而考,傳說:“當元泰定時,順寧始歸版圖,適建斯橋,故名。又說,昔勐氏土官某,渡此馬蹶,溺水以死,其民取歸天化神之義,名橋以紀念之”。
關於勐公祠,也只能在《順寧府五部志》裏一睹風采了。該志記載:一在府城城隍廟側,一在府東嶽廟左。明知府勐廷瑞以誣死。萬曆間昭雪,請封,聽民立祠,每歲春秋仲月上戊日祭。勐公祠緊靠城隍廟和東嶽廟,祭祀時間與城隍同日,這兩座勐公祠由官方建立的可能性很大。現在鳳慶縣五保山的廟裏,鳳慶城隍與勐土司同在主殿並列而坐,一起受當地人的供奉祭祀。
老家詩禮鄉永複村平路組與魯史鎮鳳凰村交界地,有一尊石頭,每到年關都有人前去祭祀。被當地人稱為勐神。傳說就是後人為緬懷勐廷瑞以石為祭性質的活動。
時間是歷史最公允的判官。勐氏雖然被滅,隨之而來的是歷史上較為著名的
十三寨起義,明萬曆二十五年(1597),順寧府推行改土歸流,布朗族土知府被革職,所屬13寨布朗族極為不滿,憑據天險,聯合附近各族人民起義,殺指揮、千百戶等官兵數十人,聲言據順寧、蒙化(巍山),攻騰越、永昌(保山地區)。後被明巡撫雲南右都禦史兼兵部侍郎陳用賓發兵鎮壓。
康熙三十九年(1700),順寧府知府董永芠編成的《順寧府志》將勐廷瑞納入《忠烈傳》,在《壇廟》中記錄了勐公祠,首次將勐公祠與東嶽廟、真武廟等一同列入群廟,在猛公祠後備注“順寧土知府”字樣。勐公祠正式出現在地方誌中,且明確記載勐公即順寧土知府,勐公祠已與東嶽廟等一樣成為官方認可的群廟。這意味著很可能此時的勐公祠已獲得官方認可,地方官府也開始了將勐土司信仰納入國家祀典的努力。此外,《順寧府志》還收錄了當地流傳的一些軼事,比如遺老所說的猛峒地,因勐廷瑞屈死而被灣甸土知州占地不歸,在《忠烈傳》中,收錄《萬曆野獲編》所言金甲人托夢靈應故事,表明其“忠順無異,原無叛志,負屈族誅”。知府董永芠還特意寫了一首《吊勐廷瑞》:
心直如弦事已休,轉將彝俗化神州。英魂總在誰招得?黃葉滄江兩岸秋。
從這首詩中,表達了董永芠這類地方官員觀念中,當時的順寧府已變為與中原一樣的地方,瀾滄江中游地域社會完成了轉型,由“彝俗”進入了“神州”,但為了顧及地方社會情緒,他仍需表明勐廷瑞的英魂還在,需要招撫的立場。這亦說明,在康熙年間,順寧府內勐廷瑞靈應已成為一種共識,有著廣泛的信仰基礎,並逐步把當地人的解釋和認知融入到地方誌等文獻之中。雍正《順寧府志》將猛廷瑞寫入“鄉賢傳”,與天啟《滇志》、康熙《雲南通志》中列為鄉賢的猛廷瑞祖先勐蓋、勐卿等並列,並用大段篇幅為其寫傳。給勐廷瑞“少喜曠俠,信任不疑”等肯定評價。在傳記中轉抄《府志餘抄》關於順寧改土歸流和陳用賓順從民意立祠祀勐廷瑞的論述,且創造了一種新說法,大意是,順寧改流後,“郡州之彝旣喜得歸大化,而亦深痛勐酋之屈於死也。”未幾,陳用賓“稍稍覺之,乃聽民間立祀,且為請封得贈中憲大夫、資治少尹。”清代地方官府書寫中的歷史詮釋,不僅使猛廷瑞沉冤昭雪,而且獲得明朝皇帝冊封,為將“聽民立祠祀”上升到了官方祭祀地位提供了更豐富和更具說服力的解釋依據。
當然,地方官府為了確立勐廷瑞信仰的正統性,除了主導相關地方化論述、杜撰皇帝冊封和知府設神牌祀之外,還需要通過靈應故事來迎合本地民眾的心理訴求,建立與地方社會的利益關係,以維護自己的統治。
如果說打開《徐霞客遊記》,是出發,那麼,掩卷沉思,則是收穫滿滿的歸來。想起摸黑進店的徐霞客,正襟危坐,心無旁鶩,那些力能扛鼎,勁透紙背的文字,便從一豆油燈的光亮裏跌跌撞撞分娩,於是我才能從386年前的荒蕪上看見葳蕤。如果他能肆意鋪展,那一定會有許多東西供我享用,只是這個邊走邊記的大旅行家非常懂得節制,寶墨都交給山水。捧讀《徐霞客遊記》,無法言說的安寧與幸福非常妥帖地簇擁著我,在這個春寒料峭的深夜,從朋友家的定親儀式上撒出,就想呆一會,靜一會,而徐霞客遊記給了我這樣的機會。如果你能夠細心地研讀遊記,這些文字就會開口說話,有氣息,有色彩,有味道,有聲音。循著歷史的聲線,神秘的勐氏脈絡漸漸清晰。晚年徐霞客義無反顧踏上了遠赴西南的萬裏征途,他的命運因此成了獨特的軌道,擺脫常規的羈絆,因此得頂巨大的孤獨抓力。鳳慶行程11天半,徐霞客唯一的遺憾就是沒能在茶房寺停下來,了卻實地訪晤的心願,當然也是宿命吧,這時他身上的宿疾隱約想犯,他的整個鳳慶的行程就有些匆忙了。再讀,我還是感謝,這些浸滿地氣的文字,不管是他拔鍋起灶還是與人品茗,不管是他日記裏蟲聲汪洋恣肆的夜晚,還是街市墟場買米煮飯。即使瑣事再多,今年還得再走。在某個惠風和暢的春日 ,悄悄出發,沿著徐霞客遊線,踏堪、探尋、緬懷,會讓自己的內心變得豐贍起來。
最新生活新聞
-
推生活導師制接住神經多樣性青少年 籲政府建構支持
(44 分鐘前) -
新營區自辦防災士課程21日登場,韌性社區攜手提升防災能量
(45 分鐘前) -
明高溫飆破36度!下週恐有熱帶擾動發展 「這天起水氣增」2地有雨
(57 分鐘前) -
你跑步我捐糧 金光明寺復蔬路跑捐1,700公斤助弱勢
(1 小時前) -
台北萬華剝皮寮:光影斑駁的時光回音/丁倩
(1 小時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