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徐霞客有交集的鳳慶人/許文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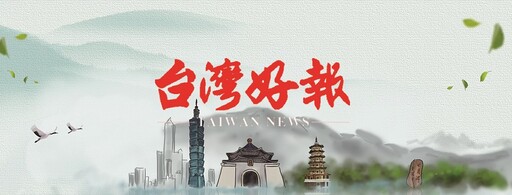
許文舟
古人雲:“五十而知天命。”年屆五十的徐霞客卻“知天命”而“不認命”。他說:“餘久擬西遊,遷延二載,老病將至,必難再遲。”於是,從明崇禎九年(西元1636年)九月至崇禎十三年(西元1640年)六月,也就是其51歲至55歲期間,他進行了一生中時間最長、行程最遠的一次旅遊,被稱為“萬里遐征”。其中,他在廣西、貴州、雲南等西南地區停留日久、所記甚詳,撰有《滇遊日記》等。
徐霞客於1639年八月五日從永昌抵達鳳慶,在鳳慶的12天裏,寫下了一萬多字的遊記,涉及人文地理、民俗文化,在有限的篇幅裏,後人都知道,徐霞客還結識了一批鳳慶人,這其中既有潛心佛法的僧侶,也有愛茶如癡的老翁,還有社會苦力,從徐霞客的“遊記”裏,這又是明朝鳳慶的另一種風景。
徐霞客在鳳慶遇到的第一個人,是習謙當地人。當徐霞客正考慮去縣城找一個挑夫,於是他便在習謙街子上打探,結果雖然問得一夫,但要價很高,且只能次日起程。“是日下午至駝騎,稅駕逆旅,先覓得一夫,索價甚貴,強從之。”因為沒有其他選擇,徐霞客也就勉強訂了下來,然後往南行走到錫鉛驛,在那裏入住。初六那天,前一天問好的挑夫按時前來,徐霞客“付錢整擔而行;以一飯包加其上,輒棄之去,遂不得行。”唉,擔子本來就已經很沉,挑夫再看到徐霞客又將一包飯加在擔子上,便不樂意了,乾脆就撂下擔子走人。徐霞客的擔子有多重,沒有具體的數字確認,但肯定少不了生活用品、被褥、筆墨紙硯、酒器、茶盞以及一路上獲取的奇石贈品食物等,這些物品盛裝在兩個用竹子為材料編制而成的箱籠,方便挑擔。
這真是百無聊賴的一天,徐霞客只能在習謙街上漫無目的地走著,當然還得再落實挑夫,雖然有人願意挑擔,但索價很高,徐霞客只能悶悶不樂地回到住處,再將沒完成的日記續上。初七日這天一大早,前一天撂下擔子罵罵咧咧離去的人再回到錫鉛驛,說可以幫徐霞客挑擔。徐霞客心想,可能沒找到活兒吧,要不,去時那種決絕斷然是不考慮回頭了。徐霞客也沒說什麼,吃完飯便讓挑夫跟著自己上路。
徐霞客在鳳慶結識的第二人是一葦法師。初七日下午,徐霞客一行從習謙趕到龍泉寺,已是人困馬乏,饑腸轆轆。“時寺中開講甫完,僧俗擾擾,餘入適當其齋,遂飽餐之而停擔於內。”徐霞客沖著寺院去,主要是這一段走下來,還是寺院能夠蹭到住宿吃飯,這天也不例外,當徐霞客一行邁著沉重的步子跨入龍泉寺門檻,剛剛講經完畢的僧侶們正圍著餐桌吃飯,徐霞客也不客氣了,端起飯碗開始飽餐一頓。當晚徐霞客也就住龍泉寺了,第二天天亮,他本想去拜謁講經的僧侶,結果房門虛掩,主人不在,只好悻悻離開。然後到雲縣轉了一圈,十一日,“覓夫未得,山雨如注,乃出南關一裏,再宿龍泉寺。”逗逗轉轉,徐霞客再來到龍泉寺。十二日一大早,徐霞客再安排顧僕進城找挑夫,自己則去見講經的僧侶,結果在這裏他鄉遇故知,見到了此前曾在永平慧光寺見過一面的一葦法師。
“十二日飯於龍泉。命顧僕入城覓夫,而於殿后靜室訪講師。既見,始知其即一葦也。為餘瀹茗炙餅,出雞葼松子相餉。坐間,以黃慎軒翰卷相示,蓋其行腳中所物色而得者。下午,不得夫,乃遷寓入新城徐樓,與蒙化妙樂師同候駝騎。”
因為在永平慧光寺相識,此時的徐霞客與一葦已是算故人相遇了,當然,一葦法師的熱情可想而知。他不僅拿出寺院裏最好吃的雞樅與松子享用,還煮茶烤餅給徐霞客,甚至將自己珍藏多時的名人黃慎軒的字畫也拿出來給徐霞客欣賞。《順寧府五部志》記載:“順寧多雞樅,以形似名,六七月大雷雨後生沙土中,或在松間林下,新鮮者多蟻蟲,間有毒,出土一日即宜采,過二三日即腐敗,香味俱減矣。鹽而脯之,曬乾寄遠,以充方物。或熬液為油,味尤香美。”一葦法師上桌的雞樅牽出了一段鳳慶特色美食雞樅的往事,不知道是“熬液為油”的油雞樅,還是“鹽而脯之”的幹雞樅,時隔386年,再讀遊記,雞樅的香依舊在字裏行間縈繞。松子也一樣,屬於鳳慶特產,檀萃在《滇海虞衡記》裏寫道:“松子,為滇果第一。”兩樣特產都在每年七八月間收穫,恰好都讓徐霞客遇上。
1639年3月廿四日進入永平,最先遇見的是慧光寺,便踅進去參觀禮佛。過後,他欲上寶臺大寺遊覽,僧人翠峰對他說:“施主,大寺已焚毀於年內的臘月,您看後,還是返回敝寺過宿吧。”徐霞客感激地答應下來。在慧光寺,撞見一位陌生的僧人正同翠峰說著話兒。翠峰見徐霞客,向他打招呼說:“徐施主,貧僧為您介紹一下,這位是從四川趕過來的一葦大師,特意趕到寶臺山來拜訪同鄉了凡大師。”又轉身向一葦介紹徐霞客,“這位是從南直隸來的旅遊狂人徐霞客先生。”接著對徐霞客說,“趕巧您回來,可否與貧僧一道陪著去拜訪了凡大師?”徐霞客一邊同一葦施禮見面,一邊高興地答應了翠峰。了凡本為寶臺大寺僧人,因寺焚毀後只得暫棲萬佛堂,徐霞客三人一齊趕過去。
兩位大師見面,當然會聊一些充滿佛理的禪語。徐霞客在旁邊,憑著自己豐富的佛學素養,聽出了他們倆存在的某些不足,“凡公禪學宏貫,而心境未融”、“葦公參悟精勤,而宗旨未徹”。在徐霞客的眼裏,他倆只能馬馬虎虎地算個僧人:“山窮水盡中亦不易得也。”可見,徐霞客的佛學知識有多麼宏富。三月廿八日起來,徐霞客準備離開寶臺山,他的下一個目標是保山。翠峰和尚派了二個僧人給徐霞客權作挑夫,約定送到永昌府城。他謝別翠峰和尚從慧光寺出發,過瀾滄江抵達永昌水寨。想不到五個月裏,一葦與徐霞客都行走在天地之間,徐霞客在永昌呆得長了些,而一葦一路行走,最終在鳳慶的龍泉寺落腳。
徐霞客在鳳慶認識的第三位人,是八月十一從雲縣歸來在東山寺遇到的來自魯史的僧人,為聽講經來到龍泉寺,聽經結束後,這位僧人被東山寺的和尚邀請
吃飯,就留在東山寺。“下閣,入其左廬,有一僧曾於龍泉一晤者,見餘留同飯。既飯而共坐前門樓,乃知其僧為阿祿司西北山寺中僧也,以聽講至龍泉,而東山僧邀之飯者。為餘言,自少曾遍曆撾龍、木邦、阿瓦之地,其言與舊城跛者、新城客商所言,歷歷皆合。”撾龍、木邦,今緬甸撣邦東北。阿瓦,今緬甸中部伊洛瓦底江中下游地區。試想,明朝時就到過緬甸這些地方的人,是怎樣的特立獨行,才能完勝歸來。
只在龍泉寺飯局上見過一面,這位來自魯史的僧人便記住了徐霞客。而當徐霞客來到東山寺時,不僅熱情地請徐霞客一同用餐,還落落大方地給徐霞客講了他遊歷緬甸的事情。說到瀾滄江流向,這位僧人的話與在雲縣舊城的瘸子、新城的客商所說的,清清楚楚全都相合。這就是徐霞客的嚴謹之處,至此,他對瀾滄江的獨自入海找到了確證。循山問水、溯江探源是貫穿徐霞客畢生旅行的一個主題。為了弄清瀾滄江真實流向,早在1637年七月二十七日到達廣西玉林,徐霞客日記裏首次出現“瀾滄”。1638年四月二十五日在貴州,徐霞客對民間所謂的“瀾滄橋”作了辯解。1639年三月二十八日,徐霞客第一次過瀾滄江,由永平進入保山。為了更進一步接近瀾滄江流向,從保山到鳳慶再到雲縣,雖然遇不到想要遇的楊州尊,卻在當地人的口中得到瀾滄江流向的正確答案。
瀾滄江古稱蘭滄,藏語拉楚,意為“獐子河”,源出青海省唐古喇山脈崗果日峰的紮曲,流至昌都後始稱瀾滄江。瀾滄江流過雲南的迪慶、怒江、 大理、保山、臨滄、普洱、 西雙版納等七個州、市,由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勐臘縣出境後稱湄公河,流經 老撾、 緬甸、 泰國、 柬埔寨、 越南五國,注入中國南海。這些是今天的人們對瀾滄江教科書式的基本認識。可是在明代,人們對其不勝了了,就是官修地理總志《大明一統志》(以下稱《一統志》)對瀾滄江流向的記載也是含糊其辭、語焉不詳,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對此,徐霞客深表懷疑而提出了他的見解。但是由於缺乏實證,他沒有充足的理由指正志書之誤,破除陳說, 所以在他西南萬裏遐征的最後歲月,以他一貫的“賈勇而前”的精神,決定專程追問瀾滄江的流向。瀾滄江是徐霞客一生最後考察的一條大江。崇禎十二年(西元1639年)農曆八月初九日午飯時分,徐霞客踏入雲州,“飯於舊城”。飯後向東,過城北順寧河砥柱橋走向雲州新城,入雲州東門,見“州治前額標‘欽命雲州’四字,想經禦定而名之也。”。在當天的遊記中,徐霞客說明了雲州之行的目的:“餘初意雲州晤楊州尊,即東南窮瀾滄下流,以《一統志》言瀾滄從景東西南下車裏,而於元江府臨安河下元江,又注謂出自禮社江,由白崖城合瀾滄而南。餘原疑瀾滄不與禮社合,與禮社合者,乃馬龍江及源自祿豐者,但無明證瀾滄之直南而不東者,故欲由此窮之。”
然後他又補敘了在雲州舊城向跛者詢問瀾滄江流向的結果:前過舊城遇一跛者,其言獨歷歷有據,曰:“潞江在此地西三百餘裏,為雲州西界,南由耿馬而去,為渣裏江,不東曲而合瀾滄也。瀾滄江在此地東百五十裏,為雲州東界,南由威遠州而去,為撾龍江,不東曲而合元江也。”於是始知撾龍之名,始知東合之說為妄。長期以來,瀾滄江的流向問題如梗在喉糾結於心,一路追尋考察無果,直到雲州舊城,終於有人明確無誤地回答了他的疑問。徐霞客並不滿足於這個結果,於是他又繼續展開調查,結果一位前來此地謀生的江右人所述與舊城跛者所言一致。至此,徐霞客“乃釋然無疑”,而在十一日,徐霞客上順寧東山寺,與四天前在龍泉寺相識的一位遊方僧人相遇,兩人共進午餐,閑坐門樓話遊歷。當徐霞客得知僧人從小就遊走於瀾滄江下游偏僻之地時,就不失時機地再次詢問瀾滄江下流的情況,想從僧人口中證實他在雲州三問的準確性,結果“其言與舊城跛者、新城客商所言,歷歷皆合。”這對於一位長期孜孜以求、鍥而不捨、不遠千里步步追問,志在尋得山水真脈的旅行家、地理學家來說,真是莫大的欣慰!確認了瀾滄江下游的流向,徐霞客一身輕鬆,但也歸心似箭。
徐霞客在鳳慶認識的第四位是梅姓老人。
“又下二裏,而宿於高簡槽。店主老人梅姓,頗能慰客,特煎太華茶飲予。”
店主破能慰客一句,說明梅姓老人在陌生客人面前顯得從容淡定,總能找到交談的話題,這讓遠道而來的徐霞客感覺良好,儘管一路上喝到了不少的茶,就是鳳慶的太華茶讓他心滿意足。老人提壺、續水,做得乾脆利索。水起水落之間,茶葉舒張,碧波蕩漾的茶水,彌漫著清幽幽的芳香。淨杯,潔器,老人做得慢條斯理,他怕怠慢了客人,邊操作邊找些話題。聊天中他知道,眼前是一位貴客,但是除了茶,他還能拿出什麼呢?
先倒一杯,敬天,再一杯端到徐霞客面前。徐霞客接過茶杯,聞香,香似沿途沾衣的稻花,不濃不淡,沁人心脾。輕輕啜飲,香是味蕾上蕩漾誘惑,他不敢輕易下咽,人生百般滋味,都在其中。徐霞客閉目頜首,讓茶香遊蕩於五臟六腑,盈盈繚繞,連說三聲:好茶!好茶!好茶!一路走來,徐霞客嘗遍各地名茶,就是在來高梘槽的前兩天,他也喝了不少好茶,在龍泉寺,一葦法師給他煮茶烤餅,在東山寺,來自魯史的僧人同樣約徐霞客喝茶吃飯。這是什麼茶呢?徐霞客弱弱地問老人。老人略作沉思說,不特殊,就種在家裏的幾畝薄地上,取其春尖一芽二葉,親手揉撚製作,叫太華茶。
懸月為燈,靜靜地朗照高梘槽,隱約間,有盈盈的念佛聲隨風而過。一個鶴髮童顏的主人,一個蒼須微顫的遠客,圍著火塘而坐,溫水慢煮,輕舉杯盞。老人顯得篤定、慈悲,飽含禪機。徐霞客則顯得睿智、虔誠,毫不諱言對茶的親近和膜拜。算不上風雲際會,可他們這一遇,雖然沒有悱惻纏綿的情感在裏面,卻留下了幾多謎讓後人去挖空心思破解,但是有答案了嗎?沒有。
其實,早在明朝時,鳳慶就有栽種茶的記錄。最早記鳳慶茶名氣較大的是玉皇閣茶。明朝時,玉皇閣是一座重樓疊閣、飛簷相啄、結構緊湊、玲瓏別致的傳統木結構大屋頂建築。在玉皇閣周圍均種有茶,尤其在它正西方的鳳山,是有名的鳳山茶。清·張弘《滇南新語》中記載:“茶產順寧府玉皇閣,一旗一槍,色瑩碧,不殊杭之龍井,唯香過烈。”清·王昶《滇行目錄》稱“順寧茶甘香溢齒。雲南茶以此為最。”玉皇閣茶最出名的是一款叫“鳳山雀舌”的春茶。鳳山雀舌茶,因形狀小巧似雀舌而得名。其香氣獨特濃郁,是以嫩芽焙制的上等芽茶。與當時的“鳳山春蕊”“明前春尖”號稱順寧三大茗品。太平寺茶是順寧在明朝的名茶,與玉皇閣茶齊名。《滇海虞衡志》載:“順寧太平茶,細潤似碧螺春,能經三瀹,尤有味也。”清代《滇行日錄》等也都溯及鳳慶茶葉。據《滇南新語》記載,早在明代,鳳慶就能用手工製造出太平茶,其色、香、味可與龍井茶相媲美。《順寧府志》“順寧雜著”記:“楚僧洪鑒來此……建立禪院,名太平寺……其岩穀間,偶產有茶,名太平茶,味薄而微香,較普茶稍細,色亦清,鄰郡多購,覓者,每歲所產只數十斤,不可多得。”原寺早已毀壞,而後又有善心人士複建,當然規模早不如舊寺。茶香在歷史中蕩漾,雖然有的名茶不過是一種追憶,但確實是這些茶,還原了一個地方茶葉發展的明晰歷史。感謝一片葉子,經受了世人的盤剝與蒸煮,留下了時光的真味,也留下一個地方與一片茶葉耳鬢廝磨的依戀。
徐霞客在鳳慶認識的第五個人,也是僧人,來自巍山的妙樂禪師。兩人相遇於新城的徐家客樓,因為都要往巍山趕路,因此兩位一見如故。可能前來鳳慶講經,妙樂禪師是巍山冷泉庵的僧人。
十二日下午,“不得夫,乃遷寓入新城徐樓,與蒙化妙樂師同候駝騎。十三日與妙樂同寓,候騎不至。薄暮乃來,遂與妙樂各定一騎,帶行囊,期明日行。”
十二日下午,找不到腳夫,只得把寓所遷入新城徐家的樓中,與巍山的妙樂禪師一同等候馬幫。十三日,與妙樂同住 ,等候馬幫沒到。傍晚才來,便與妙樂各自講定了一匹馬,帶行李,約定明天上路。從鳳慶到巍山辛苦自不必說,好在跟著馬幫走安全,相信徐霞客與妙樂也是一路上有說不完的話,但徐霞客都沒有記錄,原以為這樣平常的開始,也就是路人伴侶而已,想不到在巍山冷泉庵,妙樂禪師會對徐霞客那樣好。徐霞客在巍山城過了兩天愜意的日子,也算是對他一路艱難跋涉的犒勞吧。這當然離不開妙樂禪師,十八日從冷泉庵早晨起床,徐霞客命令顧僕同妙樂禪師去找馬幫,約定在明天動身。他老先生卻急忙吃過飯,走出北門,策馬去遊天姥寺,因為騎馬去,才能往返。妙樂禪師點燃燈火相等,於是吃過飯躺下。一句“入城,妙樂正篝燈相待,乃飯而臥。”側面說明,妙樂對徐霞客的尊從與敬仰。天黑了,人還未歸,妙樂也是焦急,於是點燃燈火,直到看見一身疲憊的徐霞客摸黑進門。十九日,徐霞客就要離開巍山了,妙樂禪師拿乳線贈給他,他也把俞禹錫的詩扇,另外作了詩贈給他。頭天講好的馬幫來到,立即吃飯後告別,妙樂禪師送出北門。兩人的關係可見一斑。
徐霞客在鳳慶認識的第六個人,便是茶房寺的僧人。
1639年八月十六日中午,徐霞客過了新牛街,坐船渡過漾濞江,到了北岸,順江而行十裏到“有兩三家倚岡而居”的馬王箐,再行五裏到“有兩三家踞岡上”的哨寨猛補者(今蜢濮者)。舊《雲南通志》記載:“在府東北二百四十裏。山極高峻,奇石玲瓏,怪異萬狀,上有聚落,名蜢濮者。”徐霞客望見路邊的山崖上有一座壯麗的三重飛閣寺廟,心為之搖盪,於是決定繞行遊覽,可是,馬幫卻要走自己的路。有好景在前,怎可放過?徐霞客獨自奮勇急攀幾裏險途趕過去。到了寺院前,他看到“就崖為壁,而綴之以鐵鎖,橫系崖孔,其前飛甍疊牖,延吐煙雲”的靈岩寺。寺僧隱庵十分好客,見有遊人,便“瀹茗留榻”挽留。徐霞客也有對“實為勝地”的靈岩寺有一種“恨不留被襆於此、倚崖而臥明月”的衝動,但他擔心“駝騎前去不及追及”,只得戀戀不捨地告別隱庵,急匆匆地去追趕馬幫。匆匆一晤,徐霞客便記下了茶房寺的美:“閣乃新構者,下層之後,有片峰中聳,與後崖夾立,中分一線,而中層即覆之,峰尖透出中層之上,上層又疊中層而起。其後皆就崖為壁,而綴之以鐵鎖,橫系崖孔,其前飛甍疊牖屋脊飛翹,窗戶重疊洞開,延吐煙雲,實為勝地。”
“隱庵為瀹茗留榻,餘恐駝騎前去不及追,匆匆辭之出。”
茶房寺還在,經過後人的多次修葺,鋼筋替下了鐵鏈,螺絲加固了卯隼,題詩添了紅漆,石級填充了水泥。徐霞客只是匆匆看了一眼,便記下了茶房寺的美:“閣乃新構者,下層之後,有片峰中聳,與後崖夾立,中分一線,而中層即覆之,峰尖透出中層之上,上層又疊中層而起。其後皆就崖為壁,而綴之以鐵鎖,橫系崖孔,其前飛甍疊牖屋脊飛翹,窗戶重疊洞開,延吐煙雲,實為勝地。”
茶房寺下麵的茶馬古道是“順下線”(順寧到下關)保留得最好的一段,清晰的馬蹄印是蓋給歲月的章戳,盛滿了剛剛落過的雨水。厚積的枯枝敗葉,頑強的苔蘚,怎麼也覆蓋不了漸行漸遠的馬幫留在歷史中的背影。寥寥數語,茶房寺的僧人便躍然紙上,在徐霞客遊記裏遇到的無數僧侶中,這位僧人只算得上與他匆匆一晤,然而,卻給徐霞客印象非常好,以致讓徐霞客心生滯留的念頭。不是因為寺舍的精美,而是由於好客真誠的僧人一見如故的緣起。
最新生活新聞
-
彰化榮服處拜會大葉大學 提升退除役官兵就學職涯管道
(1 小時前) -
新竹區監理所x竹縣府x芎林鄉公所 芎林鄉幸福巴士啟航提供4條路線
(1 小時前) -
迎51長假福建來金旅遊人潮 金門縣府強化小三通航班應對機制
(1 小時前) -
竹市春季校園就博會壓軸登場 90家企業釋出3,000職缺搶才
(1 小時前) -
臺東榮服處×華山基金會鏈結在地老人關懷服務
(2 小時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