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文學同行的擺渡人/樊時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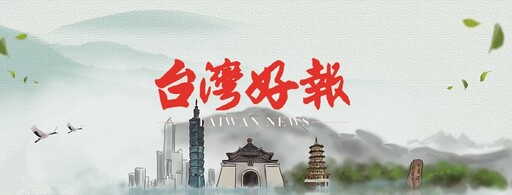
樊時勇
1985年高考前夜,月光穿透集體宿舍的黴潮,在鐵架床間織就寒涼的綢緞,如《飛鳥集》所言“夜的沉默如深井”。蜷縮於被褥摩挲作文本時,“情真意切”的朱批突然灼痛指尖——恍見母親俯身縫補的剪影,頂針在煤油燈下泛著暖黃微光。那些被“假大空”批語擊落的少年心事,此刻方悟:文字的真諦不在鉛印範文,而在粗布褶皺裏蟄伏的人間煙火。正如葉聖陶所言:“教育是農業,不是工業”,文學的種子,原該在生活的土壤裏悄然萌發。
大學校園的五四紀念牆前,自己的散文《歷史與現實》雖獲嘉獎,卻像標本蝴蝶困在系主任的恒溫展櫃。直到2023年米易中學的早春裏,詩人學生翁志勇眼瞳躍動的星火,燒穿了博物館的玻璃罩。“真正的文學當是荒原野火”,我將泛黃獎狀夾進《野草》扉頁,未名湖的漣漪正將霓虹揉碎成粼粼的歎息。這讓我想起魯迅的警語:“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原來教育者的使命,在於守護這簇火種。
大學畢業豪情萬丈,但初到寧南中學時,粉筆灰常在暮色中凝成霧靄。當浮誇修辭如幽靈重現學生的作文本,我望見了困在應試範本裏的昨日之我。效法陶行知“解放眼睛、雙手、頭腦”的教育理念,我決定將歷史長河化作墨池,引導學生以散文為舟輯穿梭古今。當《考試報》的“學思園”漸次綻放的稚嫩篇章,恰似春溪衝破冰封的脆響,很多學生找到了自己閃光點。即便2008年漂泊異鄉暫失航向,但當2025屆學生的低迷如陰雲壓境,我斷然取出塵封的火石,再次決定引導學生培育自己的閃光點,點亮心燈,恢復激情。因為教育本就是“一棵樹搖動另一棵樹”的永恆事業。
2024年的某個霜晨,初見張雅琪的《蛻變》第七稿,墨蹟裏蜷縮的蛹正經曆蛻變,學生的學習狀態發生巨變。我的批註如同精准的手術刀,讓學生文學表達漸達佳境。當晨曦漫過油墨香,我忽然懂得:文學原是蘸著心頭血殼。我們圍爐打磨的豈止修辭?那些勾畫在《奔月詩文》及《睢州文藝》校樣上的批註,分明是寫就的祭文,正如羅曼·羅蘭所說,“真正的光明決不是永沒有黑暗的時間,只是永不被黑暗所遮蔽罷了”。窗臺壘起的青玉色樣刊,每冊扉頁都迴響著破繭的顫音。
斜陽為學生文章的推薦信箋鍍上青銅包漿時,校園的小葉榕投影正化作水墨舟楫。曾在《考試報》“學思園”試翼的少年,後來的人生均展現出輝煌。有的以法律文書續寫正義詩篇,有的在實驗室譜寫基因密碼。他們或許永無作家頭銜,但文字賦予的思辨鋒芒,早化作劈開人生迷霧的利刃。這讓我想起朱光潛的教誨:“文學是人格的流露,一個文人必須是一個人,須有學問和經驗所鑄就的豐富的精神生活。”去年深冬,當學生的朗誦聲驚起寒鴉,翻飛的詩稿竟與母親當年的粗布窗簾疊印成永恆。
整理曾經的泛黃照片時,二十歲的我與學生隔河相望。他困在數據迷宮,我鬢染粉筆雪,但我們共用著子夜鍵盤驚飛宿鳥的悸動。歲月長河湯湯,所有真誠書寫都是留給時間的漂流瓶。裏面永遠藏著那團穿越時空的暖光,等待點亮某個迷途少年的眼睛。正如泰戈爾詩雲:“生命不是過程,而是永恆與刹那的交匯”,教育的真諦,正在這代代相傳的星火擺渡中。
最新生活新聞
-
-
深夜自撞分隔島!小港警迅速處理沿海路交通事故
(37 分鐘前) -
台南321巷藝術聚落 7/1起平日下午開放戶外區
(39 分鐘前) -
太平洋高壓影響!下周各地高溫炎熱 這2日台北高溫恐超過37度
(50 分鐘前) -
港湖盃3X3籃球賽開幕 蔣萬安:可從小培養選手
(51 分鐘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