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膠泥脫範本(外一篇)/劉光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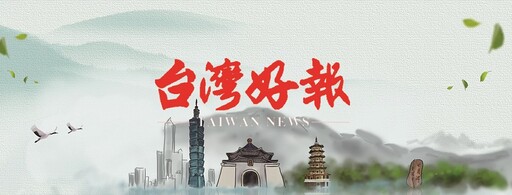
劉光軍
我出生在一九六零年代,幼時可以玩得遊戲不多,非是不愛遊戲,而是生活不像現在這麼豐富。記憶中的“脫範本”似乎是貫穿我整個童年的一項主要的遊戲活動了。我總是在平時撿些破鋪襯、爛套子,積攢的多了,就等串鄉貨郎來了,只要是聽到貨郎的鑼聲,不管是在幹什麼,我都會不管不顧地奪門而出,手裏拿著平時撿拾的那些“寶貝”,跑到貨郎跟前去換幾個“範本”。
那是一種用泥土燒制的帶有各種圖案的東西,只有薄薄的一片,圖案也多為人物或動物。玩的時候先到村外去挖一些膠泥回來,再用水把泥和好,然後在一塊較平整的地面上開始反復摔打,直到變得軟硬適中,泥團表面變得異常光滑為止。最後取上適量的一塊,用手均勻地壓在“範本”內,壓好後,再在手上輕輕磕一下,泥片就會自動從“範本”上脫下來。把脫好的東西放在房頂上或空曠的院子裏的太陽底下曬乾。這個過程就叫做“脫範本”。
什麼時候產生的這個,沒有人知道,也好像從來沒有人去關心過、質疑過,年代久了,鄉下就從這項活動中衍生出了一種俗語。就是見到有兩個長得一模一樣的人時候,就會說,這兩個人就像是從一個模子裏磕出來的,就是脫胎於此。
另外還有一種遊戲,叫做“脫泥錢”。方法是用兩枚古銅錢,中間夾一小塊泥巴,用力一擠,去掉銅錢,剩下的就是“泥錢”了,這個過程叫“脫泥錢”。有時候泥和得軟了,中間的“方孔”都被糊滿了。以致鄉下看見誰家的孩子長得太胖了,把眼睛都擠沒了的時候就會說,這個孩子活脫脫的就是個“沒眼兒的泥錢兒”。
由此可見,來源於生活的語言是多麼的鮮活、生動、有趣。
◆小時候,我也捅過馬蜂窩
早年農村的孩子,特別是男孩子沒有捅馬蜂窩經歷的恐怕不多。我小時候也是如此,見了馬蜂窩就捅。
記得七八歲的時候,村北面是一大片洋槐樹林子,遮天蔽日的。林子中間是小沙河古道,荒草叢生,野花遍地,野鳥亂飛。其中有一種叫“串地靈的”的小鳥很特別,總愛飛在空中,懸停在那裏鳴叫,聲音清脆、婉轉,十分好聽。而別的鳥好像沒有這個本領,只能停在樹枝上鳴叫。有的鳥有時候飛著也能叫喚一兩聲,
可也沒有懸停在半空中連續鳴叫的能耐。到了夏天,林子裏很陰涼,大人小孩都喜歡沒事的時候到林子裏玩。河道中間沒有樹,兩邊卻都是茂密的樹林。林子中間偶爾有幾叢灌木,多為荊棘之類的。
有一天,我和小夥伴們正在那裏玩的時候,忽然看見有一顆酸棗樹上搭了一個很大的馬蜂窩,我們就想把他捅下來。先是想用火燎,後來還是決定直接用棍子捅。商量好之後就回家吃中午飯去了。
下午,我們幾個人帶了一根長長的棍子,再次來到酸棗樹下。我們學著電影裏那些當兵人的樣子,一人編了一個柳條帽子做掩護,慢慢地從樹下的草叢裏爬過去。我第一個爬到了樹下,悄悄地伸出了木棍,剛捅了兩下,就看到有兩只馬蜂順著棍子飛落下來,就像是電影裏俯衝下來的戰鬥機一樣。說時遲那時快,就在它們飛到我的耳朵旁邊的時候,我趕緊扔了木棍,用手拼命的去驅趕,但耳朵上還是被蟄了一下。我不管不顧地跳起身來,玩了命的向林子外面跑去。回到家裏的時候,天已經黑了。我由於心裏有鬼,也不敢到明亮的地方去,怕被大人發現。就忍著疼,悄悄地趴在炕上睡了。
第二天一早,我感覺再也瞞不住了。因為耳朵和那半邊臉都腫了起來。這時候才被母親發現,她只是看了一下就完了,也沒有吵我。因為那時候的孩子不像現在的孩子那麼金貴,出現一點點狀況一般大人都會大驚小怪的。那時候的孩子真的都擁有很多自己的空間。
還有一次,我和兩個小夥伴一起在家裏玩。玩著玩著就爬到了東“杈子”的“花柴”垛上。偶爾一抬頭,竟差一點點就頂到一個搭在房梁上的超大的馬蜂窩上。我看到馬蜂窩上,爬滿了密密麻麻的大馬蜂,可把我嚇得夠嗆,趕忙往垛下爬去。奇怪的是那些馬蜂都沒有動,好像是沒看到我似的。估計是它們沒有感覺到危險吧,所以才沒有攻擊我。但是,它還是被我給毫不留情地捅掉了。這次戰鬥似乎還異常順利,誰也沒有負傷。那個馬蜂窩特別大,足足有頭號鍋蓋那麼大。它是我所見到過的最大的馬蜂窩,沒有之一。
注: 串地靈的。當地對百靈鳥的土稱。
杈子。當地指已部分倒塌的舊房子。
最新生活新聞
-
母親節將至 安德烈慈善表揚15名媽媽傳遞溫柔力量
(6 小時前) -
高市表揚多力媽媽 感謝每位媽媽 母親節快樂
(6 小時前) -
觀光局攜手高雄32家旅宿業推母親節優惠
(6 小時前) -
高雄警眷獲頒全國警察模範母親 柯志恩親自拜訪祝福母親節快樂
(6 小時前) -
中山醫大暨附醫攜手資誠 打造生醫創新與資本整合平台
(6 小時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