蟬聲中的清涼貼/王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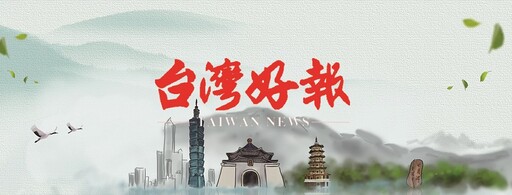
王涵
七月的太陽潑下來,就把天地烤成了銅盆,蟬聲便是盆底咕嘟咕嘟的氣泡。起先它們還怯生生地試音,像誰家孩子剛學吹口哨,沒兩下便撒了野,扯開嗓子鋪天蓋地地唱。那聲音細得能勒進肉裏,又亮得能割破熱浪,一嗓子接一嗓子,把整座村子兜頭罩住。
江南的蟬沾了水汽,調子軟得能掐出水來。陣雨剛走,柳條還滴著露珠,新蟬躲在裏頭唱,尾音拖得很長,像玉盤裏滾著的水珠,叮叮咚咚往人耳朵裏掉。嶺南的可就沒這麼秀氣,嗓子劈了叉似的,夾著熱浪往人臉上拍,劈裏啪啦砸在芭蕉葉上,聽得人心裏直冒火。最妙的是中原老廟裏的——那聲音就沉得很,撞在寺牆上又彈回來,繞著柏樹轉圈。蟬越吵,廟就越靜,像是所有鬧騰都被紅牆吸進去,釀成了一壇子啞口的幽涼。
天擦黑,鄉野就變成了偷獵場。玉米葉子刷啦刷啦地響,村民的手電筒光在青紗帳裏亂鑽。屏住氣,循著漸弱的“吱——”聲,手往樹幹上一扣,就是個胖墩墩的“知了猴”。山東人叫它“金蟬子”,淮北人直接喊“猴兒”。這土裏憋了七八年的小東西,翅膀還黏在背上,圓圓滾滾,正是肉最肥的時辰。
灶膛裏的柴火劈啪笑著,油鍋見了它們正是歡實的時候。鹽漬過的蟬蛹往鍋裏一滾,“滋啦”一聲,油花炸成金珠。只眨眼功夫,灰撲撲的蟲兒就披了層琥珀色甲,蜷成小元寶。夾起一個趁熱咬,“哢嚓”殼裂了,裏頭的嫩肉冒香,還帶著雨後土腥和熟堅果的甜。要是再灌一口冰啤酒,冰碴子混著熱油,暑氣當場就消散了七分。
淮北人家的鍋灶卻另有章法。他們用麵糊裹了蟬蛹下鍋,一碰熱油就會蓬成金紗,咬開脆殼,裏頭肉汁燙得人直跳腳。白鬍子爺爺眯著眼笑:“一只猴頂三只雞!”娃娃們哪管燙,搶得滿嘴油亮,笑聲把屋簷下的蜻蜓都驚飛了。
往南走到滇南,集市上飄著草藥香,蟬殼也可以入藥。老藥師竹匾裏平平整整地攤著蟬蛻,薄得像指甲蓋裏的月亮。有道是“伏天心煩,它比涼茶管用。”如果回家撕三片竹葉,揪兩根燈芯草,和蟬殼一起扔進砂鍋,藥湯煎成墨玉色,最是解暑。喝一口,苦裏帶涼,像有山風順著喉嚨往下灌。
晌午最躁的時候,村口老樹下,竹榻上的老人搖著破蒲扇打盹。問他嫌吵不?他抬抬眼皮笑:“蟬唱它的,我涼我的。聽久了,心火倒被它澆滅了。”那排山倒海的聲浪撲過來,人反倒像沉進井裏,燥熱慢慢往下墜,只剩井壁滲出的涼氣往上冒。
天真正黑透時,蟬聲才開始抽絲,一聲比一聲遠。曬透的棉被被收進櫃,漢子們蹲在門檻上灌薑茶。竹籠裏的新蟬偶爾撲騰兩下,翅子刮得籠子“嗞啦”響,像給田野裏最後的合唱打拍子。簷角生銹的鐵馬叮噹一聲,把白日剩下的熱渣子全敲碎了。
等第一陣金風掃過,蟬就啞了。可油鍋裏封著的酥脆,藥屜裏躺著的空殼,樹蔭下那片刻的透心涼,都成了壓箱底的寶物。等冬天西北風拍窗戶,摸出罐油浸的金蟬——“哢嚓”咬開,哪是吃蟲子?分明是嚼了一嘴七月正午的日頭,飄散出的泥腥氣都帶著當年的燙。
莊子笑夏蟲不可語冰,可它偏在黑暗裏熬了十七年,就為這九十天把嗓子唱啞。人吃它,聽它的歌,竟把最苦的三伏天,釀成了冬天舌尖上的一口回甘。蟬聲是鐵匠的錘子,年年七月,把滾燙的日子敲成一顆亮晶晶的露珠,涼得人難忘夏蟬清響。
最新生活新聞
-
-
雲林榮服處長照專題教育訓練 強化衛政體系橫向聯繫
(5 小時前) -
台南老爺行旅「台灣鯛·魚你有約」美食節開跑 鲜美滋味盡在這
(5 小時前) -
南臺科大與基隆商工簽署MOU!合推技職教育AI轉型×跨域創新人才
(5 小時前) -
基層服務暖心!高市表揚特優暨資深里長
(5 小時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