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埂上的幸福感/唐勝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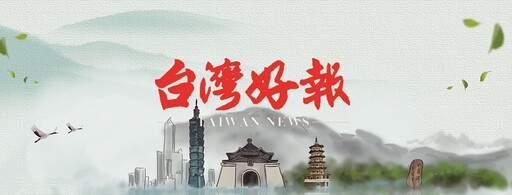
唐勝一
晨露還掛在稻葉尖上時,我總愛蹲在陽臺擺弄那盆仙人掌。刺扎手的疼,讓我想起十歲那年在田埂上摔的跤——褲腿撕破個洞,混著泥水的血珠滲出來,倒比灶台上那碗寡淡的南瓜粥更有存在感。
那時的天,高高的藍得發脆。我背著比書包還沉的豬草筐,踩著露水往家趕時,能看見三伯公佝僂著腰在水田裏插秧。他的脊樑像被歲月壓彎的扁擔,每往前挪一步,泥水就漫過腿肚子,在身後漾開一圈圈漣漪。“小子,”他偶爾直起身捶捶腰,“等你長大了,就不用遭這份罪嘍。”
我當時不信。就像不信娘總愛說的那句“好日子在後頭” 一樣,——灶台上的油罐見底時,娘總用陶瓷調羹刮著罐底,把那點油星子全淋在我那碗紅薯拌的米飯上。
八十年代初,改革的春風吹到我們村時,我正光著膀子在曬穀場曬穀,用腳掌走行像犁一樣的翻曬稻穀,那曬熱的穀粒燙得腳掌很不自在,雖說活計輕鬆,卻不如在水田裏幹的涼快,而水田裏蚊蟲叮咬、螞蟥吸血,令人防不勝防。總的來說,當農民面朝黃土背朝天,就沒得輕鬆的活計,你就得累死累活。不過,出集體工、“吃大鍋飯”的弊端,農民是敢怒而不敢言。直到上頭的政策有所改變,農民才翹首以盼。當分田到戶的那天夜裏,我爹破了往常的習慣,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乾脆爬起來,摸黑去了分到的幾畝水田田埂上站了半晌,大概是興奮著有了自家的田地,能自由自在地耕種經營。
耕田種地,辛苦的要命,最累的時候,我真的躺在泥地裏哭過。新插的秧苗在風中搖搖晃晃,像無數雙眼睛瞅著我。遠處炊煙慢悠悠地升起來,帶上燃著的柴火焦糊味刺鼻得很。我仰望著天上的片片白雲,它們飄得那麼的輕,那麼的閑,突然就想:啥時候我能不用再跟泥巴較勁呢?
那時的幸福很具體。是趕墟日偶爾能買到的半斤油豆腐,金黃的方塊泡在醬油裏,能下兩大碗飯;是過年時娘偷偷藏在枕頭下的兩塊水果糖,糖紙在被窩裏窸窸窣窣響;是第一次進城看到的電燈,拉一下繩子就亮,比煤油燈體面多了。
命運的轉彎來得猝不及防。九十年代某個清晨,我背著蛇皮袋進城時,腳下的土路突然變成了柏油的。後來我到城裏的老同學家做客,我坐著了軟乎乎的沙發,睡上了舒爽的席夢思,吃著了冰箱裏冷藏的凍雞凍魚凍肉。直到我進城工作,也有了這般一應俱全的家俱和美食時,幸福得不多久,反倒膩了,懷念起鄉村那種樸素的幸福感。
有一次回鄉下老家,我發現大伯公的兒子正用插秧機在田裏作業,機器“突突突”地跑,一天的活計抵得上過去的半個月。
村口的曬穀場改成了廣場舞場地,當年一起割稻子的嬸子們穿著花襯衫,合著音樂的節拍扭得正歡。“你看我這金鐲子,”三嬸撩起袖子給我看,“城裏金店買的,比你叔當年給我的銀鐲子亮堂多了。”她們的笑聲脆生生的,驚飛了枝頭的山雀子。
去年,我帶倆外孫去吃自助餐。面對滿桌的海鮮,小外孫未動筷子就皺眉:“外公,怎麼沒有草莓蛋糕?”“蛋糕麼,等下去買。”我由此突然想起童年時揣在懷裏的水果糖,糖紙都被體溫焐軟了,也捨不得立刻剝開吃。可現今的娃兒哪愁沒的吃,只愁不張口啊!
社區花園裏,遛彎的老夥計們總愛爭論哪個年代最幸福。肖老師說六零年代吃食堂不用自己做飯,李師傅懷念八零年代單位分房的日子。我一般不摻和,只是看著夕陽把我們的影子拉得老長,像當年田埂上那串歪歪扭扭的腳印。當農民的經歷雖然很苦很累,但很充實很豐富,是筆人生收穫,增添了一生的精彩——酸麻苦鹹甜,全部嘗個遍。
大外孫拿著最新款的手機刷視頻,突然抬頭問:“外公,你們那時候沒手機,玩什麼哪?”“看書唄,或者聊天唄。”隨後,我指著天邊的雲彩給她看,且說:“你看那晚霞,顏色跟我當年在田裏看到的一模一樣,紅得像燃燒的火焰。”她並無多大反應。
我說她:“你年少不懂,有些快樂,是不用充電的。”
大外孫這才似懂非懂地點點頭,繼續低頭刷著螢幕。
晚風穿過樹梢,帶來一陣熟悉的稻花香。我知道,有些滋味,沒嘗過苦的人,是品不出甜來的。就像那盆仙人掌,要挨過扎手的疼,才能在貧瘠裏開出花來。我不後悔“生不逢時”,因為我有著對幸福的更深感受和解讀。
最新生活新聞
-
勞動部高分署職場合理調整講座 打造身心障礙共融職場
(21 分鐘前) -
大貓熊「圓圓」21歲生日重養生 蛋糕先從竹子吃
(29 分鐘前) -
盧佳慧設計紐約辦事處台灣女力之夜 繆思設計獎奪金
(30 分鐘前) -
搭公車被門夾傷頻傳 北市公運處要求落實標準流程
(34 分鐘前) -
柯文哲羈押滿週年!民眾黨走讀與警方爆衝突
(47 分鐘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