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聽冬聲/王曉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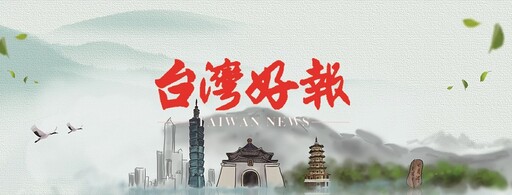
王曉倩
冬季的聲音,是須得靜下心來,側著耳朵聽的。它不像春日的鶯啼、夏夜的蛙鼓那般熱鬧張揚,它是內斂的,沉鬱的,甚至帶著幾分孤峭的寒意,卻也正因如此,格外能敲叩人的心扉。
這便教我想起古人的冬聲了。那聲音,大抵是藏在詩行與畫卷裏的。最容易想起的,是《詩經》裏“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那一份遷徙的微響,秋盡冬來,那鳴蟲的振翅聲,從曠野到簷下,再到床底,一聲聲,追著寒氣,也追著人間的暖意。唐人筆下的冬聲,則要闊大蒼涼得多。那是“夜深知雪重,時聞折竹聲”的積壓,雪是無聲地落著,但那不堪重負的竹枝驟然迸裂的“嘎吱”一響,卻像一顆石子,投在漫無邊際的雪夜的寂靜深潭裏,漾開一圈驚心的漣漪。又或是“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那犬吠是何等的焦灼與親切,它在風雪的咆哮聲中撕開一道口子,透出屋內一點如豆的燈火,以及歸人身上撲簌簌抖落雪花的聲響。這幾種聲音交織著,便是一部人間的期盼與安寧。
古時的冬夜裏,還有一種聲音,是屬於羈旅之人的。那便是驛站或渡頭的更鼓與蹄聲。南宋詞人筆下常有“馬蹄聲碎,喇叭聲咽”的句子,那碎碎的蹄音,踏在凍得硬邦邦的官道上,一聲聲,都像是敲在遊子本就飄零的心上。而遠處城樓傳來的定更鼓點,沉悶,緩慢,一聲接著一聲,丈量著漫漫長夜,也仿佛在催問著年華。這種種聲音,都帶著一種金屬般的、清冷的質地,是古典的,也是寂寞的。
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冬聲也漸漸換了腔調。如今住在城裏,冬夜的聲音,是另一種面目。窗外風的呼嘯,常被高樓切割成尖利的哨音;不再是雪壓竹枝,而是雪後清晨,汽車引擎無奈的沉悶喘息,以及鏟雪鐵鍬刮過路面時,那一聲聲刺耳的“嚓啦”。空調外機低沉的嗡鳴,成了冬日白晝永恆的背景音。這些聲音,是工業時代的,帶著一種機械的、不容分說的力量。它們似乎將冬日的嚴酷推遠了,讓我們得以在恒溫的室內安然度日,但不知怎的,我有時卻會懷念起那需要側耳細聽的自然之聲。那種聲音裏,有天地間最真實的呼吸。
我們聆聽冬聲,或許並非只為辨別風的等級或雪的厚薄,而是在聆聽一種生命的節奏。冬日的萬籟,無論是蕭瑟還是溫暖,本質上都是一種“收斂”。草木斂藏生機於根土,動物斂藏活力於巢穴,天地斂藏繁華於一片素白。而那寒夜裏的每一聲響動——風的號叫,雪的飄落,乃至屋內爐火的微吟——都是這巨大收斂過程中,生命依然存在的證明。
只要我們的心中,還能為那一聲犬吠而感到溫暖,為一聲折竹而體會靜寂,為一聲親人的呼喚而覺得慰藉,那麼,無論身處的時代如何喧囂,我們總能在這四季的輪回裏,為自己尋得一處安頓靈魂的“冬聲”。這聲音,不在遠方,就在我們認真生活的,每一個當下。
最新生活新聞
-
-
20項化粧品含蘇丹紅 食藥署重罰原料商500萬元
(41 分鐘前) -
澎縣府攜手氣象署 簽寒害預警服務合作備忘錄
(42 分鐘前) -
嘉義樹木園修復卡關 立委王美惠爭取經費到位陳駿季下令加速辦理
(44 分鐘前) -
國土署:馬太鞍溪堰塞湖35萬元慰助金 申請至11/30
(45 分鐘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