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歲,致我們曾經的青春/劉工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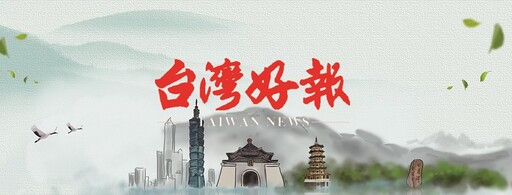
——看老電影《藍色大門》《17歲的單車》有感
劉工昌
放學了,一個女生推著自行車,短髮,風卷著她的裙角。一個男生推著自行車來到她身旁,長髮,夕陽映著他的臉。
留下什麼,我們就會變成什麼樣的大人。男孩說。
你這是聽誰說的?女孩說。男孩沉吟著,沒有回答。
不跟你說,我要回家了。女孩說。
我也要回家了。我比你快。男孩說著用力的往前蹬了一下,自行車一下竄出去老遠,忽然車頭猛地旋過來,幾乎要貼著女孩的臉。
如果有一天,或許一年後或許三年,如果你開始喜歡男生,你要第一個告訴我。男孩說。
迎著夕陽,女孩慢慢的抬起頭。夕陽餘暉映照下的她,微闔著雙眼,像一株夏日雨後的睡蓮,純潔而安靜。
小士,看著你的花襯衫飄遠,我在想,一年後三年後五年後,我們會變成什麼樣子呢?由於你善良開朗又自在,你應該會更帥吧。(畫面音)
芸芸眾生,誰有資格許誰一生,沒有人猜得中結局,一切隨風而去。
女孩子笑了。
從見面時的驚訝到喜悅,直至最後離別的傷感。女孩用脆弱的矜持維持著臉上的笑容,眼波之下,竟是巨大的情感波瀾,一浪一浪,完結在轉身後無言的告別禮中。
她似乎看到了多年後,他站在一扇藍色的大門前,下午三點的陽光,他仍有幾棵青春痘。她跑向他,他笑著沖她點點頭。(畫面音)
她閉上了眼睛,雖然看不見自己,但能清晰的看見他。
夜色裏,她被風中的自由氣息所吸引,興奮地瘋跑。她睡著在自己編織的夢境裏,嘴角是因滿足而揚起的弧度。街道邊,她大搖大擺地邁著步伐,長椅上,她慵懶迷糊的沉睡。
三年五年以後,甚至更就更久以後我們會變成什麼樣的大人呢?是體育老師,還是我媽?-(畫面音)—
曾經的那個時候我們什麼都不懂,可當我們什麼都懂後卻失去了可以做夢的時光。
小士,這場以謊言開場的邂逅,我從來不曾後悔。我沒猜到開頭,因為我來不及排練,不過早早的猜到了結局。
這是臺灣電影[藍色大門]片尾的一段對白。2002法國坎城影展最受年輕人歡迎的作品。
兩個17歲的高中女生是親密無間的好朋友,一個女孩告訴另一個說她喜歡同校的一個男生,但卻不敢說出來。男生總愛一個人夜裏偷偷的到校游泳池游泳,她拉著最要好的同學到那裏悄悄看他游泳,聽他發出水聲也好。當最要好的同學大著膽子把她的想法告訴男生時,她卻害怕得逃走了。
可是男生喜歡上了那個向自己表白的女孩,而女孩卻又陷入了最親密的友情和隱隱的想要拒絕卻又難以割捨的異性情愫的矛盾間,經過了一系列的誤會碰撞,當下午三點的陽光溫柔的打在藍色大門前時,他們卻走到了門口,已到了各自要上路的時候了。
青春變成了一個輕盈的轉身。可是,一轉身就可離開的人,也許一輩子也無法忘記,有些人一轉身就不見了,但就是無法從你的視野中消失。
這也許就是一種成熟,一個很痛的詞,它不一定會得到,卻一定會失去。
因為他們已不再是那個穿著磨破了衣襟的舊衣服,劃損了手腕也要挽留一段無望的感情的17歲,而是那個要轉身離去,再也不能屬於你的歸人。
電影其實真的是在規勸,勸你把失去的感覺看作一場幻覺,騙你人生那麼長,失戀那麼短,街上繞一圈就能碰到另一個有情人。所以他們始終自持克制,甚至因為終於可以結束一段糾纏輕鬆釋然。
還是林夕說得好,你喜歡一個人,就像喜歡富士山,你可以看到它,但不能搬走它。
其實有時固執地想要得到真實,卻不知道很多時候會好受傷。
納蘭性德曾說,月似當時,人似當時否。
許多時候,一株沉默的枝椏上,總是註定無法迎來一朵矜持的花。於是,一段故事在那個夏日的黃昏戛然而止,再也沒有後來。
想起了從前看《羅馬假日》,結尾男主人公獨自憂鬱的站在欄杆前的一幕。當鏡頭從遠處拉伸,整個空曠又莊嚴的教堂穹頂投在他頭上方,他只手插兜,輕風拂過憔損的臉頰,頹然折返,無視世界地一步一步前進,直到走過了,一整段羅馬的時光。
我不想說話。當我們用十多年的時光看完一部電影後,我想說,我終於看懂了,可是又覺得,其實自己什麼都不懂;,儘管自己早已不再年輕。時間總是在我們不注意時以飛快的速度流失掉。一天中,鐘錶上指針的轉動圈數描繪了時間的輪回,那是它的寬度,而在人身上則顯示了時間的長度。
他哽咽地說:“能在那個美麗的羅馬之夏,作為赫本的第一個銀幕情侶握著她的手翩翩起舞,那是我無比的幸運。”他低下頭,在赫本的棺木上輕輕印下一吻,深情地說道:“你是我一生中最愛的女人。”在場的人無不唏噓落淚。
我曾經像所有的人一樣想像起格裏高利派克在奧黛麗赫本葬禮前說這番話時的情景。
但現實告訴我,這一切都不是真的。
真實的奧赫本在面對死亡前的一天,當兒子問她一生有什麼遺憾時,她只是說:“沒有,沒有什麼遺憾,我只是不明白為什麼有那麼多兒童在經受痛苦”。
這是真正的天使,她的一生,沒有滿足我等凡人所念念在茲的一出肥皂劇的完美落幕,卻用有限的經歷告訴我們,一個女人的美麗一定從她的眼睛中看到,因為那是她心靈的窗口,“愛”居住的地方。我們所真正不能抗拒的,只有愛與死。
再看這部電影,17歲,女孩、男孩。他們開始了自己也弄不明白的東西,沒有刻骨銘心,我們看來,似乎一切只是象他們頭頂天空一樣,清爽、乾淨,乾淨得令人心疼。
步履匆匆的人們也許該偶爾駐足,跳出來看看,自己曾經的模樣。
然而你真的很清楚的記得自己的17歲,自己是在哪個夏天成熟,變成大人的嗎?也許我們沒有人能說的清,但常常不經意間,就打開那道藍色大門,回到了那個忽然就長大的夏天。成熟是一個很痛的詞,它不一定會得到,卻一定會失去。
天是藍的,大門卻關上了。
同樣是在17歲,在海峽的這邊,卻敞開了另一扇完全不同的大門。
一個從外地到北京討生活的年輕人,與一個同樣來北京討生活的中年人和住一屋。他們在過著靜靜的絕望的生活。中年男人時常陷於冥想之中,尤其是當他隔著門縫,看著那個同樣來這裏討生活的小保姆,他的時間被拉長了。他在醒著的時候,看到了夢境。所謂的聽天由命,就是一種根深蒂固的絕望。陷入冥想中的人,不需要更多的東西,一切都已經夠了,除了沉默,就像有些人會突然看到自己職業的盡頭,知道它最好也不過是一種什麼樣的生活。
年輕人好不容易找了一個快遞工作,但他沒有單車,只好由快遞公司提供,每個月扣錢;等到最後一個月扣錢全部結束,可就在單車正式成為己有的那一天,單車被偷了。夜深人靜的時刻,他曾嘗試著去偷一輛,其結果可想而知。當他快絕望時,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他發現了騎著自己單車的新主人正和自己的女朋友情意綿綿,而自己朝思暮想的那輛車就在一旁。
這樣,一部單車將兩個十七歲的男孩子聯繫起來。一個是從農村來城市打工的鄉下孩子,懷揣著關於城市的美好夢想,卻因為單車的失竊打亂了原來設計好的人生軌跡。另一個是在城市長大的城裏孩子,雖然生活在城裏,卻是城裏貧寒的家庭,在父親屢次三番沒有履行給他買單車的承諾後,偷了家裏的錢,買了鄉下孩子被偷的單車。當他為心愛的女同學把車鏈條上好,目送著她到門前回頭與自己微笑著告別後,從未有過的願望登時一下全實現了。開始了真正的青春肆意時刻。只見他右手揮舞著西裝,左手平攤,飛快蹬著自行車,在人來人往的大街上肆無忌憚。
但他永遠也不會想到,他用來酷炫青春的單車是另一個農村孩子在陌生的城裏賴以生存的夢。農村孩子歷經艱辛找到了被偷的車,再偷回來,卻是一次當眾被打且遭搶回的淩辱。他設法再偷走城裏孩子的車回到公司,經理兌現了重新錄用他的承諾,他的夢終於勉力得以延續。不過,他很快被城裏那幫孩子找到。
那是一個午後,又像是黃昏。霧靄後面忽然浮現出來的太陽,是恍惚的,散著隱忍的光芒。在城市一個荒蕪的角落,他遭受了一群陌生的城裏孩子的淩辱:拳打、腳踢、吐唾沫後揚長而去。那廢棄似又人影憧憧的城市一角,他孤零零的躺在那裏,仿佛此時的他是另一個在童年嬉戲的自己。這裏就是童年時的家鄉。
他跑到城裏孩子家再度要回自己的車,兩個素昧平生的少年卻也結下了難以化解的怨。當他在沒人的街角以一個孩子所擁有的最後一絲做人的尊嚴換回了車與城裏孩子一人一天使用的命。城裏孩子希望以車炫技換回暗戀女友的青春夢,農村孩子希望以車的繼續使用維繫快遞公司上班的命。有那麼一天,當那個城裏小子終於向這個快遞小子伸出了友好的手,同時卻用一塊磚頭砸碎了自己的愛情。
慌亂中,這群年輕人追逐著,手舉著磚頭、或者木棍,在狹窄破敗的巷子裏。那個買車的孩子倒下了,滿頭是血,這是個令人毫不意外的結局。看著他沒法站起,無助的伸出手去的那個動作,是孤獨的青春尋求援助的聲音。除此之外,我們還不斷的看到孩子們崢嶸著臉孔廝打奔跑的時候,街上的那些大人們在木然觀望,沒有絲毫的訝異,他們平靜的看著這群孩子賣力的編演那幕叫青春的鬧劇。
這樣的安排讓兩個17歲的孩子帶著無助的哀怨與無盡的挫敗感,兩個無法交談的人,只能通過那輛已血跡斑斑的自行車背後那個虛幻的世界溝通。鏡頭拉近那個城裏孩子的臉,他躺倒在街頭,看向更遠的地方,鏡頭映出他疲憊的臉頰,與剛才倔強冷笑的神情完全不同。面對近在咫尺卻熟視無睹遠去的路人的無情,他的臉顯得更加絕望而脆弱,他的身邊,只有那個農村孩子一雙驚恐的眼一直在注視。兩個如此接近的人卻隔著千山萬水,就算登高眺望也無法看到對方的身影。這樣的疏離來源於他們看待世界的態度,一個在現實,一個在遠方,其實他們都想靠近彼此,但是人與人有時候就是無法溝通,儘管他們都只有17歲。
與恨無關。當這個可憐的城裏孩子被打的爬不起來時,那個在一旁瑟瑟發抖的快遞小子站了起來,悲痛欲絕的他撿起地上的板兒磚狠力地朝砸車的人拍去,對青春的揮別,竟是這麼一塊不起眼的板兒磚。只有在這凝聚了全身仇恨和憤怒的一拍,他才真正變成了大人,象一個遠古時代遭受重創的劍客,在人頭洶湧的都市裏,他單薄的背影註定要顯得十分的落寞與蒼涼。
新約聖經尖銳地指出,神所要求我的,和我的本相相比,差距何止千裏。即使最自大的人,若能窺探一下,就不難發現在他狂傲的臉孔底下,其實隱藏著更深的恐懼,怕自己不足和無能。
最後,當這個曾經的快遞小子在他曾經的死敵城裏小子和周圍城裏人群近乎木訥的佇望中,異常艱難卻堅定的扛起那輛幾成廢鐵的自行車,緩緩穿過繁華的馬路,向人群深處走去,身後留下了一片血跡,幾聲歎息,還有那永遠也無法說清的17歲的年齡。車流如梭,人們按自己既定的軌道向前,沒有人會在意這樣一個孩子和這樣一部單車。
街上尖銳的喇叭與路人冷漠的注視相互輝映。都市街頭熾熱的陽光下,活著的方式黯然交替,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言不由衷。快遞小子扛著車把目無表情的徑顧向前,不知還能否遇到那個跟他一樣經歷過愛而選擇死亡的人。
這是第六代導演王小帥的影片《17歲的單車》。當我們變成成人後回憶過去時,我們總是希望能聽見那些荒涼的調子。青春,有多少人,曾經只為了這兩個字,就構成了熱淚盈眶的理由。可在這裏,只有淒厲的尖叫,還有那些因為一再激怒而恐怖的面容。看著他們,時常想起身邊已經目擊與正在目擊的那些孩子,也許還有曾經的自己,已經消耗永不複返的過去。青春,除了遠方,還有什麼呢?
王小帥收起了青春的憂傷,他甚至不給死亡很多的時間; 他只是給出這群孩子還有他們身邊每個人自己的生活,告訴人們是什麼將他們推向極端行為,極端的極限是什麼,以及它的背面會是怎樣深淵一般的無力。
他慣用的長鏡頭伴隨著敘述者仿佛冷漠而漫不經心的目光凝視著主人公之間的情感糾葛。這些技法的運用帶來一種遊移不定的漂泊感。在頻繁的人造景觀甚至人造都市的堆積疊壓中,人物的安然處身之地到底在哪里呢?他們曾經在家鄉的生活已經割斷,而新的生活是否總要重臨起點,重臨初到北京的那個自行車修理攤?沒有銜接的生活斷層終於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個漂泊的身影,愛情決不是合理的解脫與歸宿。
但有愛總是好的,就像那個佔有單車的新主人,那個長在普通工人家卻有著一顆倔強而敏感的心的孩子,在其女友毅然投身比自己強大的多的對手的懷抱,挽留的努力近乎自焚的舉動中,他決然選擇了以抗爭來尋求愛的完滿,儘管結局最後變的如此淒涼,然而在聽著他倒在牆邊那幾句含糊不清的呻吟詞,我們仍然喘了口氣。他還沒有死去,也就還有愛的權力,儘管在我們這個時代,愛者與被愛者註定屬於兩個世界。
在一群底層男人注視中,片中的兩個女人是那麼的飄渺,遙不可及。那個破舊的自行車攤,在那對叔侄貪婪卻又真純的目光糾纏中,一個令人著迷的“城裏”女人閃現了,俊臉白膚紅唇花衣,這只是一個保姆,她神秘的來,在這兩個沒怎麼見過漂亮女人的農村人心裏劃下一道模糊的影線,卻又神秘的離去,周迅扮演的保姆沒有一句臺詞,但弦外之音足以令人唏噓。
而另一個女孩子,是那個年齡段男孩子看到後就永遠也無法把心挪開的人,她的長相和氣質幾乎是完美的,她對感情的處理似乎也是完美的。她是如此的沉靜,如此的珍惜自己的初戀,她對那個寄予了自己初戀的男孩的挽留得不到應有的迴響讓人直為那個不懂事的男孩駐足歎息,當她告別這些毅然心歸旁屬時我們只是遺憾,而不忍心責怪她。因為我們知道,一切終將過去,似乎早已註定。 她的扮演者叫高圓圓,不知道象不象那時候的她自己。
在看慣了一些“國際巨星”們咬著牙齦將冷酷進行到底的形象後,在這個女孩身上終於找到了我們所需要的美麗。那種純淨,那種柔弱,那種挽留後的憂傷,是如此清晰的刻在我們業已麻木的心裏。只可惜過於短暫,因為她只有17歲,她的名字叫青春。我們之所以認為女性的青春是如此美麗,是因為我們內心深處知道年輕女性註定要在時間鋸齒的撕咬中失去這美麗,我們知道要保留這美麗的一切努力都將受到時間的嘲弄,不管你願不願意,也不管你是否做好準備,你沒法拒絕時間,拒絕成熟。
看見時間的殘酷施加在這個單純的孩子身上比自己體驗它的殘酷更加驚心動魄,沒有什麼比看見這樣一個女孩背離大家的心願離開單車小子而投入另外一個男孩懷中更具震撼力的了。在這些孩子身上,一直保持著近乎倔強的自尊。在揚眉吐氣以後,他便有了些脆弱的驕傲,還有長期被別人看低所釀就的自卑。成長就是接受失望和接受自我的過程,我想我們很多人都曾經是影片中的兩個孩子, 用最鮮活最真純的青春跟這個世界碰撞過。後來的我們 越來越不得承認 這個世界不是誰都幸運的遇到一個可以在自己迷茫的時候用力推一把的人。
我們只能呆呆的看著那個可憐的男孩因為自己的任性而錯失了生命中最該留住的東西,待到他醒悟後開始挽留時,挽留的悲劇早已註定。是的,一切都已經確定。正如叔本華所說,一切疏忽大意都是深思熟慮的結果,一切意外的邂逅都是事先的註定,一切屈辱都是懲罰,一切失敗都是神秘的勝利。
海峽兩岸的導演為我們共同展示了17歲的兩扇不同顏色的大門。有趣的是,它們都是由同一公司臺灣吉光電影公司推出的電影產品,它們都是講幾乎同一時期的孩子關於青春的故事。
“我們會成為什麼樣的大人”,這是《藍色大門》惟一的疑問。
也許這樣一段對話可以作答。
約翰悶悶地說著,“我們只好住在海地斯。而你漸漸老去時,你會告訴那些不肯輕信的女人們說,是你開錯了抽屜。”
“這真是一場夢啊,”姬絲美仰視著星空歎息說道,“看起來多麼奇怪,身上就這麼一套衣服,和一個一文不值的未婚夫躺在這裏!”
“在星星下麵躺著,”她又說,“我以前從沒注意過星空。我總認為它們是屬於某人的大鑽石。現在它們全部讓我覺得害怕。它們讓我覺得過去的一切都是一場夢,我全部的青春。”
“那是一場夢,”約翰安靜說道,“人人的青春都是一場夢,一種化學的瘋狂形式。(《一顆像麗茲飯店那麼大的鑽石》S·菲茨傑拉德)
一切重新開始,青春戛然而止。
最新生活新聞
-
世壯運廣告「四邊包繩不打洞」 北市府:民間製作
(17 分鐘前) -
高捷乘客掉錢包誤用緊急對講機 列車停駛約1分鐘
(21 分鐘前) -
對流旺盛 新北南投花蓮山區、汐止深坑防豪雨
(27 分鐘前) -
國中會考想拿A++ 補教估英語、數學至多錯1題
(28 分鐘前) -
澎湖碧海鷗聲澎湖星光路跑登場 千人揮汗挑戰
(31 分鐘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