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訪興化第一山/夏俊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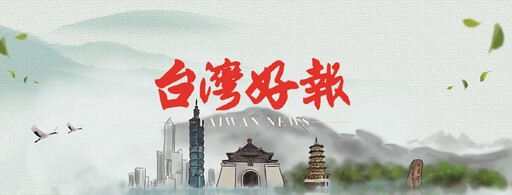
夏俊山
我在江蘇興化市工作,一晃6年,期間,讀鄭板橋的《自在庵記》,該文開頭即曰:“興化無山,其間菜畦、瓜圃、雁戶、漁莊,頗得畫家平遠之意。” 鄭板橋是清代興化人,所記不會有誤,於是認定興化沒有山。
興化地處江淮之間、裡下河腹地,境內河流如織、湖蕩星布,城區十水彙聚、水城交融,是一座水城。如果有山,該有多美啊。唐代吳融詩曰:“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寰。長川不是春來綠,千峰倒影落其間。”我一直覺得:有山無水單調,有水無山枯燥,興化如果有水有山, 肯定也是“非人寰”,甚至比富春山水還要美。
興化沒有山,我覺得美中不足,同事不以為然:誰說興化沒有山?興化城區就有座“興化第一山”——陽山,你沿著昭陽路一直向西,路的盡頭就是。
我曾多次沿昭陽路西行,送校報《文正風》給路南的楚水實驗學校,路北的楚水初級中學,繼續西行一段路,就能看到 “興化第一山”,為什麼不去探訪一下?
天氣晴好,又是週末,我騎上電瓶車出發了。很快,就到了昭陽路的盡頭。前方的路變窄了,是水泥鋪的村路。看兩邊的房子。門牌有“陽山村北山”的字樣。看來,陽山就要到了。問路邊一位老人陽山在哪兒,老人熱情地說:“就在這裡。它跟北山、南山一樣,都不是真山,我帶你去看看。”
老人叫劉正林,80歲了,在他的帶領以及介紹下,我明白了:所謂陽山,其實是昭陽將軍的墓,因墓上的封土高出周邊,形似小山,人們就叫它 “陽山”。如今的陽山村由北山、居家、王陽三村合併而來,已經改稱臨城街道陽山社區。我在興化,寓所距昭陽湖不遠。湖畔,張弓躍馬的青銅塑像就是昭陽將軍。對這位被奉為興化人文始祖的昭陽將軍,我早就有所瞭解。
昭陽名雲,字陽,楚昭王後裔,官至楚國令尹,兼任大司馬(主管軍事)、上柱國(衛戍楚都郢)。據司馬遷的《史記》以及《國語》、《戰國策》等史籍,西元前 334年 (楚威王六年),昭陽率兵攻打越國,殺死越國國君,興化一帶併入楚國。今興化城區舊稱昭陽,即源於此。興化一帶併入楚國,因該地多水,又稱興化為楚水。
毛澤東有詩曰:“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當年的昭陽將軍恰恰相反,打了大勝仗,反而選擇解甲歸田。為什麼要這樣呢?
據《史記·楚世家》:楚懷王六年,昭陽將軍移兵攻打齊國,齊王大驚,恰逢秦國謀士陳軫出使齊國。陳軫勸說昭陽適可而止,否則該得的官爵也會丟失,正如畫蛇添足。昭陽將軍聽了勸,沒有繼續進軍。楚懷王念其戰功,將“古渤海之地”,即今興化一帶封為昭陽食邑,並賜予傳國之寶“和氏璧”。後來,和氏璧為趙惠文王(前299年—前266年在位)所得,秦昭襄王“願以十五城換之。”藺相如“完璧歸趙”留下佳話。
西元前305年,65歲的昭陽去世,被加封普晉王,厚葬於封地。他的墓就在我這次探訪的興化第一山——陽山。不談興化的歷史街區和名人,只談昭陽將軍,就有成語“畫蛇添足以及和氏璧”與之有關。歷史文化底蘊如此深厚,興化成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我覺得並不意外。
有劉正林老人帶領,我很快就來到了陽山廟。陽山廟也叫山子廟,東側圍牆上有一行大字:“昭陽十二景興化第一山。 ”前句好理解。據有關史料,明景泰年間,內閣大學士高穀選點了“昭陽十景”,後來又增加兩處景觀,成為 “昭陽十二景”。“陽山夕照”是“十二景”之一。高穀有詩雲:“陽山一帶望中微,翠巘蒼崖映夕暉。斜影半侵行客騎,餘光猶燭定僧衣。樹頭鳥雀參差集,草際牛羊次第歸。明日登臨重載酒,莫令遲暮感芳菲。”
站在陽山廟外,展開想像的翅膀,我的眼前似乎出現了一幅畫面:,遠處,殘陽如血,河水粼粼,揉碎了絢麗晚霞;近處,殿宇巍峨,古墓隆起,突兀在平川之上;廟內,蒼松肅立,晚風掠過,樹梢似乎在低吟。哦,陽山,它是自然造化的傑作,也是千年歷史的載體啊!
步入廟門,映入眼簾的是昭陽殿。殿門外的楹聯為:“勃海鎮軍壓六王而霸楚,陽山食采留三戶以誅秦。”這副楹聯十分霸氣,內容顯然與昭陽將軍當年征戰有關。
據說,楚懷王六年(西元前323年),昭陽率兵攻打魏國,得襄陵等八邑,史稱“楚魏襄陵之戰”,此戰威震齊、燕、趙、魏、秦、韓六國。即“壓六王而霸楚”。楚懷王重獎昭陽,賜給他傳國之寶“和氏璧”,又將“古勃海之地” (即興化一帶)封為他的食邑。即”陽山食采留三戶”。《史記·項羽本紀》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下聯中“三戶”應該是代指楚將昭陽。
昭陽殿內,閃著金光的昭陽將軍坐像在大殿中間,其左邊(東側)是觀音殿,右邊是三官殿。昭陽將軍上方的金字為“山子府君”。
曾看到《興化日報》有文章說:“‘山子’一詞,有一古義為假山,《宋史·禮志十六》:‘大中祥符六年七月二十九日,詔輔臣觀粟於後苑禦山子。’明袁宏道《飲徐參議園亭》詩:‘藥欄斜佈置,山子幻生成。’《儒林外史》第四十回:‘三間楠木廳,一個大院落,堆滿了太湖石的山子。’這些作品中的‘山子’皆為假山的意思。”作者由此大膽推論,昭陽的“山子府君”,可能是因為其墓名“山子”而得名。(見2023年12月15日《昭陽大將軍:人生密碼》),但也有人認為:“山子”是昭陽的諡號。古代戰爭中,馬匹很重要。《穆天子傳》記載,周穆王最愛的“八駿”為赤驥、盜驪、白義、逾輪、山子、渠黃、華騮、綠耳。其中,山子是灰白色的俊馬。昭陽病死,楚烈王便以周穆王的駿馬“山子”之名為諡號,賜給昭陽,故後人稱昭陽為“山子府君”。
我更相信後一種解說。範仲淹諡號“文正”,興化就有學校以 “文正”為校名。昭陽諡號“山子”,有山子廟、山子村、山子府君等名稱實屬正常。
門外陽光明媚,殿內稍顯昏暗。拍了幾張照片,我就出了昭陽殿。殿西側的建築有西廂房,西廂房北是昭陽祠堂。昭陽祠堂與昭陽殿之間是昭陽墓。墓前,昭陽將軍的白石立像身著戎裝,劍在身後,他手握劍柄,目光如炬,威風凜凜。他的身後是昭陽墓。黑色大理石上鐫刻著隸書金字:“山子府君昭陽墓。墓碑下方是《昭陽墓誌》,有文字曰:“西元前370-325年,昭陽受楚懷王之命在興化地區鎮海口,今昭陽鎮北山子”。在此期間,昭陽帶領昭、屈、景三姓子弟在此種植、捕撈、煮鹽,繁行生息,深受當地人民擁戴……墓誌上的文字把我的思緒帶到了2300多年前。
西元前323年襄陵大捷後,昭陽將軍來到“古勃海之地”,也就是今天的興化一帶。褪下甲胄後,他成了當地民眾種植、捕撈、煮鹽的首領、指揮。晨霧散去,天空很藍,海風帶著鹹味。海面上,有藤條綁紮的浮標在隨波浪起伏,那是海邊居民的漁網;偶爾有一群白鷺掠向西飛去,下方有鹽灶升起青煙。蘆葦杆在劈啪作響,火舌舔舐著釜底,沸騰的鹽鹵析出了白色的細密晶體。繼續西飛,可以清楚地看到田埂,有人在田埂間勞作,他們的皮膚被太陽曬得黝黑,但看到抽穗的耐鹽稻時,眼神中分明有著喜悅……一年又一年,興化區域,地勢低窪,原本是一片黃海灘塗,在昭陽將軍率眾開墾後,漸漸有了變化,終於發展為《史記》中”飯稻羹魚”的豐饒之地。
興化人沒有忘記昭陽將軍的貢獻,為了紀念這位激流勇退、鑄劍為犁的興化開邑第一人,興化人修建了山子廟。據明朝萬曆十九年(1591年)成書的《興化縣新志》記載:“陽有惠政邑人祠而祀之。死葬於西山去城三、四裡高阜隱隱隆隆今俗稱山子廟者是。”
歷史上的山子廟有前後兩進高大方形大門殿宇,前殿供奉著昭陽將軍的部將(此殿及部分配套建築於明萬曆年間改為“香山寺”),後殿為昭陽殿,重簷下掛著“昭陽殿”匾額,殿內供奉著昭陽將軍站立塑像。大殿東西牆壁上彩繪著昭陽將軍率兵攻城掠地的戰鬥場景圖畫。昭陽墓位於昭陽殿西北側,墓前神道兩側排列著石人、石馬、石麒麟等。墳塋築石為臺,封土為墓,高三丈有餘,周圍二十餘丈,加上築在距地面一、二丈高的土墩上,遠遠望去猶如小山,昭陽山(簡稱陽山)即由此而來。
彈指間,滄海桑田;一刹那,轉身千年。歷史上的山子廟已經毀於戰火,昭陽墓也成為平地。劉正林老人帶領我看到的山子廟和昭陽墓是2007年之後重建的,規模小了許多。陣風掠過,廟牆後的三棵大榆樹簌簌有聲,似乎在訴說著逝去的歷史。不斷飄落的榆錢,引出了劉正林老人的感慨:“我80歲了,這幾棵老榆樹,比我年紀大,也比我有錢!”
我會心一笑,又想起《昭陽大將軍:人生密碼》一文。文中說:“走過了幾座小橋,拐過了幾條小巷,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幾條歡快的小狗,終於來到了這幾棵高大的古槐之下。“可是,我看到的卻是榆樹,地上那麼多榆錢足以證明我和劉正林老人的判斷沒錯。榆樹為什麼會被當成古槐?我想,作者大概是冬季來的。”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冬天,樹木掉光了葉子,有些樹種難辨認。我能一眼看出是榆樹,恰好趕上了榆錢飄落的時節。也許,這就是機遇吧?
陸遊詩曰:“紙上得來終覺淺。”探訪興化第一山是我的“躬行”,歸來後,我跟同事說:你說的‘第一山’,有其名無其實,不能算山。
同事狡黠地一笑:“興化確實有一座真山,叫茅山,不過,歷史上屬東臺,劃入興化後,被興化的愚公們挖山不止,挖掉了。昭陽將軍猶如歷史文化名山,說他是‘興化第一山’不能算錯。再說,要論名和實不符的現象,生活中多著呢,你管得過來嗎?”
我沉默了。
最新生活新聞
-
中市水利局積極推動水資源永續發展 盧秀燕:感謝「看不見的城市英雄」
(4 小時前) -
臺中榮總國際醫療前進菲律賓 與當地醫院及臺商攜手合作遠距醫療
(4 小時前) -
苗栗榮服處辦善後講習 精進榮民遺產管理
(4 小時前) -
雲林榮服處攜手雲縣忠愛聯誼會 溫馨關懷榮民眷
(4 小時前) -
114年全中運聖火重返臺南 十區熱情接力開啟地主榮耀序章
(4 小時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