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父親的國慶日/張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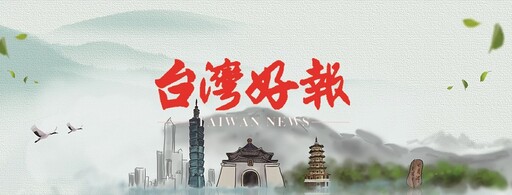
張丹
又到國慶日了,窗外的紅旗再一次掛滿了街巷,電視裏滿是歡騰的聲響,舉國都在歡慶。可這熱鬧裏,偏偏少了最盼過節的那個人-一我的父親。
父親是今年5月份走的,遠在異地工作的我卻沒能見他最後一面。懷著沉痛與內疚,我攥著車票狂奔回老屋,推開熟悉的木門,只見他靜臥在冰冷棺木中,再也不能笑著喊我小名,講那些戰火裏的故事。
抬頭望老屋的牆,還是老樣子,貼滿了幾十年前的戰爭畫報,紙邊都卷了,顏色也淡了,可那上面的士兵和槍炮,像是還在跟人說當年的事兒。堂屋正中間,父親參軍時親手繡的毛主席像還掛著,紅布底兒有些發暗,針腳卻整整齊齊的,那是他一輩子最寶貝的東西,平時誰都不讓碰。
那個斑駁褪色的老木櫃,父親鎖了幾十年,鑰匙一直藏在他枕頭下。我顫抖著拿出鑰匙,“哢嗒”一聲打開櫃門的瞬間,時光好像突然倒回。裏面整整齊齊碼著他的勳章,每一枚都泛著溫潤的光澤,邊緣的磨損記錄著當年的槍林彈雨;泛黃的參軍照片裏,年輕的父親穿著軍裝,眼神明亮得像夜空裏的星;還有那套洗得發白的軍裝,衣領處縫補的針腳細密整齊,軍帽上的五角星雖有些暗淡,卻依舊透著當年的英氣。我把軍裝貼在胸口,仿佛還能感受到父親穿著它時的溫度,眼淚再也忍不住,砸在軍裝上,暈開一小片濕痕。
父親是個苦孩子,出生沒多久,爺爺奶奶就被疾病和饑餓奪去了生命。是鄰居老太奶一勺麵湯、一口粗糧,把他拉扯大。1963年,16歲的他揣著老太奶塞的煮雞蛋,背著簡單的行囊參了軍。從冰天雪地的東北到濕熱的雲南,再到抗美援越的戰場,他把最美好的青春,都獻給了家國。
打我記事起,父親的故事就像永遠講不完的書。飯桌上,他夾一筷子菜,就能說起當年在戰壕裏啃凍硬的乾糧;家裏來客人,他喝一口酒,就會講起戰友們互相掩護、浴血奮戰的日子。他講得眉飛色舞,眼神裏閃著光,那些九死一生的經歷,成了刻在他骨子裏的記憶,他把對戰友的懷念,都融進了來之不易的、每一個平常的日子裏。
每逢國慶前夕,父親就像盼過年的孩子,興奮得睡不著。他一天好幾趟去開老木櫃,把軍裝拿出來小心翼翼展開,撫平褶皺再疊好放回;勳章和照片更是擦了又擦,直到能映出他的臉。他還攥著電視遙控器不肯鬆手。有次5歲的侄子吵著看動畫片去搶,父親竟像孩子般緊緊護著,侄子哭了,母親數落他,他卻噘嘴漲紅了臉:“他天天看,就這幾天,電視得歸我,我要等國慶看閱兵!”
國慶日當天,父親天不亮就起床了。他坐在鏡子前,用梳子蘸著水,把頭發梳得一絲不苟,連鬢角的碎發都不放過;刮鬍子時,更是小心翼翼,仿佛在完成一件重要的儀式。接著,他拿出那套心愛的軍裝,一件一件慢慢穿。扣紐扣的時候,他手指有點抖,卻扣得格外認真,指尖輕輕摩挲著紐扣,仿佛在與某個遙遠的時空、某位逝去的戰友交流。穿好軍裝,他挺直腰板,站在鏡子前打量了許久,才端端地坐在堂屋正中央的椅子上,緊緊握著遙控器打開電視。那一刻,他的眼神炯炯有神,像當年在戰場上瞄準目標時那樣銳利,眼裏仿佛燃著一團火,那是對家國最深沉的熱愛。
當電視裏傳來天安門廣場的歡呼聲,白鴿展翅飛向藍天,一列列軍人方隊邁著整齊的步伐,雄赳赳、氣昂昂地走過,父親的身體微微顫抖起來。他盯著螢幕,連眼睛都捨不得眨一下,當看到天安門城樓上國家領導人致禮時,我分明看見他眼角的皺紋裏,滲出了晶瑩的淚花。那淚水裏,有對當年歲月的懷念,更有對如今祖國強盛的驕傲。
那天的父親,一整天都浸在喜悅裏。見了鄰居,就拉著人家累叨國慶故事與戰場經歷;我們兄妹提想吃他做的紅燒肉、想要小竹筐,他都爽快答應,笑容像秋日陽光,溫暖明亮。
可今年國慶,再也沒有父親的身影。家裏電視開著,閱兵畫面依舊壯觀,堂屋正中的椅子卻空著,那個攥著遙控器的人,再也不會回來。我站在窗前,望著故鄉方向,淚水模糊雙眼。千裏之外,父親的墳塚旁,國慶的歌聲隨風飄過。我在心裏默默致敬:“爸,您看,這盛世正如您和戰友們所願!九泉之下的您,一定正和戰友們看著滿街的紅旗,聽著喧天的鑼鼓,慶祝國慶吧!”
最新生活新聞
-
-
台南聯手中央解白水溪淤積 建土方去化平台強化治水韌性
(2 小時前) -
花蓮光復災後第七天!經濟部:還缺8類用品
(2 小時前) -
屏東金同會秋節博餅聯誼 傳承傳統金門味
(2 小時前) -
高市浯江金同會理監事聯席會議 金門博餅傳承與鄉親同樂
(2 小時前)




